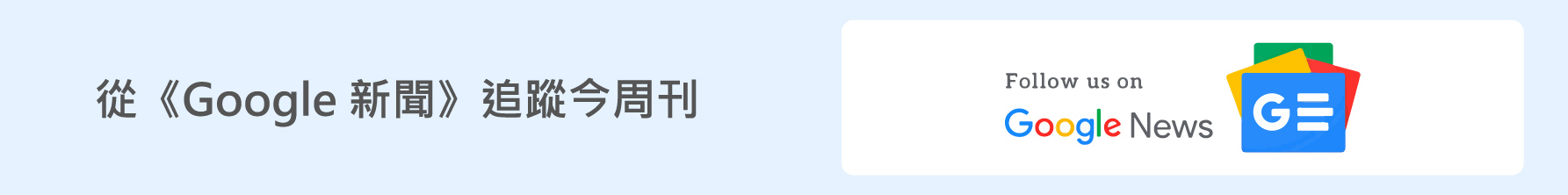多數人的交際圈和所得水準息息相關:我們鮮少認識比自己有錢很多或窮很多的人。當經濟陷入停滯時,社會上就會產生明顯的贏家和輸家,而不同族群缺乏聯繫的結果,當然會導致彼此的信任度降低。而且,在缺乏信任的情況下,很容易就會發展出交相指責的文化。這時,沒有人會聚焦在如何解決經濟及金融失靈的系統性導因,所有人都會便宜行事地將所有問題泛政治化,將問題歸咎給特定個人或族群的行為。至此,社會上的信任度隨時可能崩解,最後更可能讓經濟停滯成為一場長久的夢魘。
社會大眾開始以一種空前的速度變得興旺繁榮,從各式各樣的證據便明顯可見這個事實,例如人口迅速增加,財富甚至增加更快。美國(獨立)戰爭並未對這個進步的軌跡造成抑制,它雖讓國家陷入徹底拮据的狀態,但並未對民間企業形成阻礙:個人變得更勤懇刻苦、更有創造力,而且富裕度達到歷史新高。
..到了某種程度,法國繁榮度的上升反讓人心變得更浮動與不安;公眾的不滿遭到激化;對舊制度的憎恨則與日俱增,整個國家走向革命的傾向已顯而易見。
..被革命摧毀的體制幾乎絕對都比前一個體制更良善,而且經驗告訴我們,當惡質的政府跨出改革的第一步,卻也是它們最危急的一刻..原本人民以為各種弊端似乎無可逃避,故而耐心忍受,可是一旦他們因外力啟發而開始產生擺脫這些弊端的想法,就會變得連一刻也無法再忍受。
..一七八○年時,沒有人認為法國即將走下坡。相反的,大家都以為它的進步將浩瀚無垠,因為正好在此時,主張人類有能力持續創造更完美局面的理論才剛崛起。二十年前,所有人都不敢對未來抱什麼指望,但到一七八○年,大家卻又變得無畏無懼。人們想像自己即將在可預見的未來進入一個聞所未聞的幸運時代,所以不再珍惜眼前的幸福,一心只嚮往著新奇的經驗。
換言之,在托克維爾個人眼中,革命動亂的導因和馬克思主義分子的想法─導因於無產階級遭到剝削─並不太一致。取而代之的,他的立論基礎是:蒸蒸日上的繁榮度,自然會讓人對未來產生希望和樂觀的期待,而一旦這些希望和樂觀期待沒有被滿足,舊有的政治及社會體制就會面臨嚴厲的挑戰。如果接下來經濟還不進反退,舊有的政治及社會體制更勢必會成為眾矢之的。所以,托克維爾的觀點考慮到「期望」所扮演的角色,也考量到一旦期望未能實現,可能對政治體系造成的衝擊。
自一九八○年代以來,不民主的世界發生了許多動亂,包括柏林圍牆的倒塌、接下來的蘇聯帝國瓦解,以及阿拉伯之春等,這些動亂全都貼切呼應了托克維爾有關「期望」以及期望對政治穩定性的影響等觀點。不過,托克維爾的觀點也很適合用來解釋目前西方各經濟體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經濟停滯不盡然會讓所有人變窮,但絕對會導致很多期望落空。公共支出計畫的削減、教育成本的上升、退休年齡的提高、退休金提撥金額的增加,以及低迷的股票市場報酬等,都只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環節,而這個問題就是:經濟的停滯導致我們無法實現先前對自己許下的承諾。當千金散盡那一刻,剩下的只有失望而已。而失望過後,接下來的就是困苦、悲劇和憤怒。
二○一二年十一月,這三者在可怕的情境下同時發生:一個叫阿瑪伊雅.伊加納(Amaia Egana)的五十三歲女性因被依法強制逐出她位於巴拉卡多(Barakaldo)巴斯克鎮(Basque)的住家而自殺。這不是西班牙第一宗民眾因被依法強制逐出住宅等相關問題而自殺的案件。不過,拜那個事件發生後的一波大眾抗議潮(包括有人在一場足球賽裡高舉「他們不是自殺,而是被謀殺。銀行和政客是共犯。停止依法強制驅逐行為!」等斗大標語的旗幟)之賜,各新聞網全被相關的報導占據。
從二○○八年到二○一二年伊加納自殺的那段期間,儘管西班牙的銀行業者已獲得西班牙政府的大力支援─這當然是西班牙納稅人埋單─但還是有近四十萬棟西班牙住宅被銀行依法強制收回。另外,西班牙政府對外國債權人的鉅額負債,以及馬德里當局和半自治區之間日益擴大的隔閡,更讓原本已經非常惡劣的局勢變得雪上加霜。事實上,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場地區選舉的結果出爐後,加塔隆尼亞省(Catalonian)內主張分離主義的政黨還要求舉辦獨立公投。不過,由於加塔隆尼亞省本身也是負債累累,根本無法從國際資本市場取得任何資金,所以,他們最後還是不得不向現實屈服,心不甘情不願地繼續依賴馬德里當局提供的信用度日。
同樣的情景,我們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儘管十八世紀末期的法國已經相當進步,但骨子裡卻是個寅吃卯糧的國家。它完全沒有能力平衡財政收支,所以只好依賴一堆天真的債權人來滿足它的資金需求,但實際上它根本還不起這些債務。指券是典型為了隱匿根本財務問題而設計、但事後證明毫無價值的一種財務工具。另一個問題是,法國是個族群分裂的國家:所謂第三階級─也就是平民百姓─在政治上完全沒有發聲的空間,儘管如此,但他們卻不斷被要求為教士及特權階級的揮霍無度埋單。法國並沒有發生過等同於英國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光榮革命促成了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而這項法案也讓議會權勢凌駕於君王之上。
儘管那時法國的財富正逐漸流失,但很多「敗家子」卻還是忙著你爭我奪,所以,當然也就未能注意到平民百姓逐日上升的怨氣。他們完全未能有效處理收成不佳和食物價格高漲對平民百姓的衝擊,而且,舊有的體制在債臺高築的情況下,根本也沒有足夠的政治力量來因應最終引爆大革命的種種緊張情勢,只能若無其事地假裝「一切如常」。
斷頭臺或許早已不復存在,但如今我們卻還是能聽到法國大革命前的種種回音。食物和燃料價格同步上漲(部分導因於新興亞洲強權的強烈需求)和西方經濟的停滯,已經導致實質所得遭到嚴重壓縮。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急速下滑,但政府內部卻還是遲遲無法達成共識,採取有效的行動方針來因應種種問題。
如今,意識型態的分歧已經導致美國政治圈嚴重失和,其中,倡議大幅加稅來改善國家財政的那一派人,直接槓上決心推動降低政府的社會參與度的另一派人。而在歐元區,「第三階級」納稅人和南歐國家的失業者,則成了經濟調整方案下的砲灰,儘管就很多情況來說,政府、銀行業、外國債權人的莽撞行為,還有布魯塞爾、柏林、法蘭克福和巴黎等地的單一貨幣立法人員在歐元危機惡化時種種決策行為的後果,根本就不該由這些可憐的人承擔。當然,撙節方案所造成的痛苦也促使政治極端主義者漸漸復活。國家的傳家之寶─這裡指大型企業,而不是大面積的土地─則被一步步賣斷給外國買家。儘管如此,債臺高築的政府卻還是沒有明確的因應策略,只能被動期待經濟自行奇蹟式地恢復成長。
眼前西方國家政府當局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或許不是革命和斬首,不過,一如舊有體制的統治者,今日的政策制定者似乎也不太有能力解決我們的問題。儘管人民對公共及民間制度的信任正逐漸瓦解,政策制定者卻還是未能勇敢面對存在於「應享權益」(建立在「所得將恆久持續上升」的假設上)和「經濟停滯」之間的托克維爾缺口─也就是期望及新現實之間的缺口。
托克維爾缺口勢必會繼續惡化,因為堪稱二十一世紀初經濟及政治生活核心特質的「三個斷裂」─有錢人和貧民、不同世代之間的衝突,以及前述的債權人/債務人對立─正逐漸擴大。
在經濟快速擴張的初期,這些斷裂並不那麼攸關重大,因為在這個環境下,即使社會上的某些人變得比以前富裕非常多,但最後變拮据的人並不多。然而,一旦經濟陷入停滯,這些斷裂就會被凸顯出來,因為某處的某人最終將會失敗,贏家和輸家的對比將變得愈來愈明顯。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先前對自己許下太多遠超過自身經濟能力所能負擔的承諾,等到不得不面對現實的那一天到來,所有人只好為了搶奪戰利品而鬥爭,而那樣的鬥爭將進一步傷害彼此的信任,最後形成一種交相指責的廣泛氛圍,所有人也就很難繼續合作下去。而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停滯很可能逐漸成為永久的事實。
第一個斷裂:所得分配不均
眼前西方國家政府當局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或許不是革命和斬首,不過,一如舊有體制的統治者,今日的政策制定者似乎也不太有能力解決我們的問題。儘管人民對公共及民間制度的信任正逐漸瓦解,政策制定者卻還是未能勇敢面對存在於「應享權益」(建立在「所得將恆久持續上升」的假設上)和「經濟停滯」之間的托克維爾缺口─也就是期望及新現實之間的缺口。
托克維爾缺口勢必會繼續惡化,因為堪稱二十一世紀初經濟及政治生活核心特質的「三個斷裂」─有錢人和貧民、不同世代之間的衝突,以及前述的債權人/債務人對立─正逐漸擴大。
在經濟快速擴張的初期,這些斷裂並不那麼攸關重大,因為在這個環境下,即使社會上的某些人變得比以前富裕非常多,但最後變拮据的人並不多。然而,一旦經濟陷入停滯,這些斷裂就會被凸顯出來,因為某處的某人最終將會失敗,贏家和輸家的對比將變得愈來愈明顯。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先前對自己許下太多遠超過自身經濟能力所能負擔的承諾,等到不得不面對現實的那一天到來,所有人只好為了搶奪戰利品而鬥爭,而那樣的鬥爭將進一步傷害彼此的信任,最後形成一種交相指責的廣泛氛圍,所有人也就很難繼續合作下去。而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停滯很可能逐漸成為永久的事實。
第一個斷裂:所得分配不均
人民彼此信任程度較高的國家,通常享有較高生活水準。有趣的是,當一個國家的信任度高,它的所得分配不均程度也傾向於較低。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下稱OECD)國家來說,挪威、瑞典、丹麥、芬蘭和瑞士的信任度及生活水準都很高,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則很低。而在光譜的另一個極端,土耳其、墨西哥和葡萄牙的信任度低、生活水準低,且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較高。這麼說來,如果改善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應該就能提高信任度,或至少能讓整個社會變得快樂一點。
但是造成分配不均的很多源頭─其中最顯著的是全球化的各種動力─並非任何單一政府所能控制。此外,儘管在所得分配不均程度較低的富裕經濟體,人民彼此的信任度可能較高,但這些經濟體卻經常為了成長力道不強的問題而傷腦筋,例如,在OECD國家中,人均國民所得高且所得分配不均程度低的國家─最顯而易見的是北歐國家─從一九八○年代迄今的經濟擴張率都不高。
換言之,在自滿的社會裡,由於人民太過信任他人,所以可能缺乏承擔風險的必要動力,而冒險卻可能是促進經濟擴張的要素。對類似瑞典這種國家來說,那可能不是個問題,不過,對地緣政治利害關係較高的國家─主要是美國─來說,就是個大問題。無論如何,若經濟未能擴張,陷入「亞當.斯密型憂鬱」的風險就會上升。另一方面,若一個人均國民所得較低且所得分配不均程度逐漸上升的經濟體,能推動足以提高經濟成長率的政治改革或其他措施,那它的經濟可能相對比較容易擴張。例如中國從一九八○年代以來的經濟成就,都是拜鄧小平所啟動的改革之賜。所以說,即使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高,還是能透過經濟的快速成長來阻止亞當.斯密型憂鬱的發生。
事實上,在中國邁向成功的歷程裡,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也是日益上升的。快速發展的經濟體通常都會經歷一段所得分配不均程度迅速擴大的時期,因為在這個階段,製造業生產力遠比鄉村活兒的生產力高,所以,城市新富族群的所得會快速超過鄉村的窮人。然而,這個流程最後應該會逆轉,因為從事農業的人口會因此急速減少,結果促使剩餘農民的生產力上升,並讓他們的所得漸漸趕上遙遠城市裡的其他人。
不可否認的,國家必須發展一些政治制度來促進這個流程,讓沒能跟上第一波發展的人可以安心並耐心等待翻身的一天。不過,阿拉伯之春的種種事件顯示,由於那些國家缺乏這種政治制度,才會導致憤怒外溢,進而演變成革命和動盪。舉個例子,突尼西亞並不是特別貧窮的國家,但它的多數財富都掌握在二○一一年一月被罷免的班阿里總統(Zine al-Abidine Ben Ali)手中,導致他下台的原因之一是:他將剽竊來的數十億美元(據稱)藏在瑞士,並利用這些財富過著極盡奢華的生活。
無論如何,以人均國民所得來說,不管是中國或突尼西亞都算不上經濟大聯盟裡的一軍,而且,它們的所得分配不均程度也和一般開發中國家的典型情況不同。富裕的西方國家目前面臨的挑戰和上述兩個國家相當不一樣。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十年間,經濟成長的利益相當公平地被分配到國民手上,但從一九八○年代起,情況便大不相同。尤其是美國和英國,經濟成就的戰利品多半流到極少數人手裡,多數人並未受惠。在這種情況下,一旦經濟陷入停滯,就可能衍生嚴重的政治問題。既得利益者當然想要握緊手中的財富,但還沒獲得顯著利益的人將突然領悟到原來自己早已錯失良機,並進而產生不滿。
多數人的交際圈和所得水準息息相關:我們鮮少認識比自己有錢很多或窮很多的人。當經濟陷入停滯時,社會上就會產生明顯的贏家和輸家,而不同族群缺乏聯繫的結果,當然會導致彼此的信任度降低。而且,在缺乏信任的情況下,很容易就會發展出交相指責的文化。這時,沒有人會聚焦在如何解決經濟及金融失靈的系統性導因,所有人都會便宜行事地將所有問題泛政治化,將問題歸咎給特定個人或族群的行為。至此,社會上的信任度隨時可能崩解,最後更可能讓經濟停滯成為一場長久的夢魘。
儘管阿根廷和日本的經濟都從成長變成停滯,但到目前為止,阿根廷的經驗還是遠比日本糟。我在第一章主張,阿根廷之所以表現落後,主要是孤立主義經濟教條和所得分配相對極端不均(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所造成。事實上,從阿根廷戰後經濟相對走下坡以來,原本已經非常不平均的所得分配變得更不均。在一九五○年代至一九六○年代,該國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已經比國際標準高,但到一九九○年代以後,不均程度簡直比天還要高。
在經濟停滯和所得分配不均的雙重不利影響下,改革將會變得更加困難,阿根廷就是因為這樣,才會變成極端不利從商的國家之一。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二○一二年對各國「經商容易度」所做的排名,阿根廷在一百八十三個國家的排名中,名列第一百一十三,其中特別惡名昭彰的,是它處理建築許可、新創事業和徵稅的方式。相反的,已經忍受經濟「失落二十年」的日本卻名列第二十。看起來是因為日本國內的信任度遠比阿根廷高。
阿根廷內部極度缺乏信任,那西方國家會不會也正朝這個方向前進?當然很可能,目前很多國家所得分配不均的數字確實很令人頭痛。從一九七九年至二○○七年,所得最高那一%美國人的平均實質稅後家計所得上升幾乎三倍。而前二%至二○%高所得人口的所得則只增加大約三分之二。所得水準居中的族群─前二一%至八○%─的所得僅增加約五分之二。而所得水準最低的二○%族群,所得只增加五分之一。
更驚人的是,在二○○五年至二○○七年間,所得前二○%人口的總稅後所得,竟然超過後面八○%人口的總所得。所得最高那一%人口的稅後所得,從一九七九年時占總所得的一○%,急遽上升到二○○七年的二○%。實質上來說,已經富有的人變得超級富有。不可否認的,其他人最後也都變得比較富裕,但有錢人和不那麼有錢的人之間的缺口卻明顯擴大。換言之,美國經濟成就的戰利品多半流到已經非常富裕的人手裡。難怪在金融危機過後,「占領」運動(譯註:如占領華爾街運動)會那麼盛行。
以英國來說,在一九七○年代中期的谷底時期,薪資所得最高的一%人口占總薪資比例大約是六%,從那之後,他們的占比便大幅上升,最高達到二○○七年的一五%,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水準。就這項指標來說,英國和阿根廷的差異並不大。在彭巴草原的土地上,最富有的一%人口的所得占總所得比率,也是從一九七○年代中期開始就從谷底急速上升。相反的,日本多年來的變化並不大。在戰後時期,最富裕的一%人口占總所得的比率一直都維持在一○%以下。
就其本身而言,所得分配不均程度高並不盡然是個問題來源。在十九世紀末,一般人甚至認定所得分配不均對經濟成長有利,他們認為有錢人通常會比窮人存更多錢,而這等於是為未來的投資儲備資源。更多的投資又進一步代表新科技將會更快速推出,從而促進經濟的成長動力。就這個論述而言,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最終會和多數人(而非少數)的生活水準同步上升。所以,不足為奇的,這一派思想特別受上流統治階級歡迎。
但到二十世紀末,這種論述卻多半被唾棄,這主要是拜跨國比較之賜。誠如我們所見,世界上最富裕的很多國家─以人均國民所得衡量─的所得分配不均程度都比較低,而世界上某些最貧窮的國家,所得分配不均程度卻相當高。以某些案例來說,這些國家的統治菁英甚至建立了一種等同盜賊統治(kleptocra cies)的制度,其中兩個最顯著的例子是獅子山(Sierra Leone)和中非共和國。
市場的力量以很多其他方式,讓某些人獲得比其他人多的利益。然而,某些案例裡卻存在明顯的贏家和徹底的輸家。全球化是一種國際性的市場力量,它促使更多資金得以跨國界移動,進而使所得明顯重新分配。由於世界各地較低薪資的國家充斥大量投資機會,所以,美國製造業的工人當然不敢指望美國企業一定會在國內投資。於是,儘管中國的薪資增加,但美國製造業薪資卻面臨下調的壓力,而且美國的失業率也上升。
換言之,在自滿的社會裡,由於人民太過信任他人,所以可能缺乏承擔風險的必要動力,而冒險卻可能是促進經濟擴張的要素。對類似瑞典這種國家來說,那可能不是個問題,不過,對地緣政治利害關係較高的國家─主要是美國─來說,就是個大問題。無論如何,若經濟未能擴張,陷入「亞當.斯密型憂鬱」的風險就會上升。另一方面,若一個人均國民所得較低且所得分配不均程度逐漸上升的經濟體,能推動足以提高經濟成長率的政治改革或其他措施,那它的經濟可能相對比較容易擴張。例如中國從一九八○年代以來的經濟成就,都是拜鄧小平所啟動的改革之賜。所以說,即使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高,還是能透過經濟的快速成長來阻止亞當.斯密型憂鬱的發生。
事實上,在中國邁向成功的歷程裡,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也是日益上升的。快速發展的經濟體通常都會經歷一段所得分配不均程度迅速擴大的時期,因為在這個階段,製造業生產力遠比鄉村活兒的生產力高,所以,城市新富族群的所得會快速超過鄉村的窮人。然而,這個流程最後應該會逆轉,因為從事農業的人口會因此急速減少,結果促使剩餘農民的生產力上升,並讓他們的所得漸漸趕上遙遠城市裡的其他人。
不可否認的,國家必須發展一些政治制度來促進這個流程,讓沒能跟上第一波發展的人可以安心並耐心等待翻身的一天。不過,阿拉伯之春的種種事件顯示,由於那些國家缺乏這種政治制度,才會導致憤怒外溢,進而演變成革命和動盪。舉個例子,突尼西亞並不是特別貧窮的國家,但它的多數財富都掌握在二○一一年一月被罷免的班阿里總統(Zine al-Abidine Ben Ali)手中,導致他下台的原因之一是:他將剽竊來的數十億美元(據稱)藏在瑞士,並利用這些財富過著極盡奢華的生活。
無論如何,以人均國民所得來說,不管是中國或突尼西亞都算不上經濟大聯盟裡的一軍,而且,它們的所得分配不均程度也和一般開發中國家的典型情況不同。富裕的西方國家目前面臨的挑戰和上述兩個國家相當不一樣。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十年間,經濟成長的利益相當公平地被分配到國民手上,但從一九八○年代起,情況便大不相同。尤其是美國和英國,經濟成就的戰利品多半流到極少數人手裡,多數人並未受惠。在這種情況下,一旦經濟陷入停滯,就可能衍生嚴重的政治問題。既得利益者當然想要握緊手中的財富,但還沒獲得顯著利益的人將突然領悟到原來自己早已錯失良機,並進而產生不滿。
多數人的交際圈和所得水準息息相關:我們鮮少認識比自己有錢很多或窮很多的人。當經濟陷入停滯時,社會上就會產生明顯的贏家和輸家,而不同族群缺乏聯繫的結果,當然會導致彼此的信任度降低。而且,在缺乏信任的情況下,很容易就會發展出交相指責的文化。這時,沒有人會聚焦在如何解決經濟及金融失靈的系統性導因,所有人都會便宜行事地將所有問題泛政治化,將問題歸咎給特定個人或族群的行為。至此,社會上的信任度隨時可能崩解,最後更可能讓經濟停滯成為一場長久的夢魘。
儘管阿根廷和日本的經濟都從成長變成停滯,但到目前為止,阿根廷的經驗還是遠比日本糟。我在第一章主張,阿根廷之所以表現落後,主要是孤立主義經濟教條和所得分配相對極端不均(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所造成。事實上,從阿根廷戰後經濟相對走下坡以來,原本已經非常不平均的所得分配變得更不均。在一九五○年代至一九六○年代,該國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已經比國際標準高,但到一九九○年代以後,不均程度簡直比天還要高。
在經濟停滯和所得分配不均的雙重不利影響下,改革將會變得更加困難,阿根廷就是因為這樣,才會變成極端不利從商的國家之一。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二○一二年對各國「經商容易度」所做的排名,阿根廷在一百八十三個國家的排名中,名列第一百一十三,其中特別惡名昭彰的,是它處理建築許可、新創事業和徵稅的方式。相反的,已經忍受經濟「失落二十年」的日本卻名列第二十。看起來是因為日本國內的信任度遠比阿根廷高。
阿根廷內部極度缺乏信任,那西方國家會不會也正朝這個方向前進?當然很可能,目前很多國家所得分配不均的數字確實很令人頭痛。從一九七九年至二○○七年,所得最高那一%美國人的平均實質稅後家計所得上升幾乎三倍。而前二%至二○%高所得人口的所得則只增加大約三分之二。所得水準居中的族群─前二一%至八○%─的所得僅增加約五分之二。而所得水準最低的二○%族群,所得只增加五分之一。
更驚人的是,在二○○五年至二○○七年間,所得前二○%人口的總稅後所得,竟然超過後面八○%人口的總所得。所得最高那一%人口的稅後所得,從一九七九年時占總所得的一○%,急遽上升到二○○七年的二○%。實質上來說,已經富有的人變得超級富有。不可否認的,其他人最後也都變得比較富裕,但有錢人和不那麼有錢的人之間的缺口卻明顯擴大。換言之,美國經濟成就的戰利品多半流到已經非常富裕的人手裡。難怪在金融危機過後,「占領」運動(譯註:如占領華爾街運動)會那麼盛行。
以英國來說,在一九七○年代中期的谷底時期,薪資所得最高的一%人口占總薪資比例大約是六%,從那之後,他們的占比便大幅上升,最高達到二○○七年的一五%,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水準。就這項指標來說,英國和阿根廷的差異並不大。在彭巴草原的土地上,最富有的一%人口的所得占總所得比率,也是從一九七○年代中期開始就從谷底急速上升。相反的,日本多年來的變化並不大。在戰後時期,最富裕的一%人口占總所得的比率一直都維持在一○%以下。
就其本身而言,所得分配不均程度高並不盡然是個問題來源。在十九世紀末,一般人甚至認定所得分配不均對經濟成長有利,他們認為有錢人通常會比窮人存更多錢,而這等於是為未來的投資儲備資源。更多的投資又進一步代表新科技將會更快速推出,從而促進經濟的成長動力。就這個論述而言,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最終會和多數人(而非少數)的生活水準同步上升。所以,不足為奇的,這一派思想特別受上流統治階級歡迎。
但到二十世紀末,這種論述卻多半被唾棄,這主要是拜跨國比較之賜。誠如我們所見,世界上最富裕的很多國家─以人均國民所得衡量─的所得分配不均程度都比較低,而世界上某些最貧窮的國家,所得分配不均程度卻相當高。以某些案例來說,這些國家的統治菁英甚至建立了一種等同盜賊統治(kleptocra cies)的制度,其中兩個最顯著的例子是獅子山(Sierra Leone)和中非共和國。
市場的力量以很多其他方式,讓某些人獲得比其他人多的利益。然而,某些案例裡卻存在明顯的贏家和徹底的輸家。全球化是一種國際性的市場力量,它促使更多資金得以跨國界移動,進而使所得明顯重新分配。由於世界各地較低薪資的國家充斥大量投資機會,所以,美國製造業的工人當然不敢指望美國企業一定會在國內投資。於是,儘管中國的薪資增加,但美國製造業薪資卻面臨下調的壓力,而且美國的失業率也上升。
中國所得的提高進一步促使食物需求增加,因為隨著人民變得更富裕,通常會改變飲食習慣,從蔬食轉變為肉食和乳製品,而這兩種飲食習慣所需要的穀物量大不相同,想吃動物或動物製品,就必須耗用更多穀物來飼養這些動物,這時的穀物需要量就遠比直接用穀物餵飽人類所需的量多很多。於是,較高的食物價格又進而讓美國的農民受惠,但美國製造業工人卻又變得更貧困。另外,中國成長加速導致能源需求上升,這讓石油生產國受惠,但石油價格的上漲卻讓石油消費國的負擔增加。
另外,隨著全球化的速度在二十世紀末急速上升─這是拜金融市場開放、新(且便宜)的資訊科技及政治改革之賜─讓金融產業從業人員的所得大幅上升,但其他人的所得卻只是溫和增加。從一九五○年至一九八○年,美國金融產業的薪資大約只和美國其他民間產業的工資相當。但從那時開始,該產業的薪資便大幅上升,到金融危機爆發前的二○○六年,金融業平均薪資已經大約比其他民間產業高七○%。在歷史上,一九二○年代也曾出現如此大的薪資落差,但隨後不久,華爾街也崩盤。16
導致金融產業相對其他產業的薪資水準出現如此巨大轉變的原因不難揣測:在經濟及科技快速變遷的時期,一般人可能會更需要尋找自稱有能力為複雜金融風險(包括和新科技的不確定有關的風險)定價的人來幫助自己理財。將全球化和資訊科技革命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思考,就不難理解為何二十世紀末整個經濟體系對金融智慧(也許「智慧」這個用語不是很恰當)的需求會迅速上升了。
在此同時,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金融產業監理標準的放寬,促使產業從業人員承擔愈來愈高的風險,問題是,沒有人在乎這些風險承擔行為是否符合整個社會的長遠利益。
不意外的,承擔較高風險的做法也讓民間部門的報酬大幅上升(儘管事後各經濟體多半受到了系統性的損害)。當然,在優渥報酬的吸引下,經濟體系裡的高等教育人才也對金融業趨之若鶩。而在這些心靈手巧的生力軍的協助下,金融業又進一步發明了更多製作精巧的風險性產品。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圈的薪資飆漲,最優秀的人才都被它網羅,監理機構當然也就更無法聘雇到擁有適當能力的職員來「監管並督導」這些金融行為。
在此同時,由於世人愈來愈積極追求更高的收益率,金融服務的需求也大幅上升。投資管理公司規模持續成長,但那並不是因為他們發現了讓報酬率步步高升的萬靈藥,而是因為他們必須想盡所有辦法去尋找愈來愈精巧─當然風險也愈高─的方法,來為退休金、醫療保健和因人口老化而衍生的其他需求籌集財源,所以不得不持續擴編。那些投資是否真的能創造優渥利潤?
答案是什麼,根本不那麼重要。舉個例子,投保人接受友善的獨立財務顧問的建議後,以為一切萬無一失,並開始編織安逸退休的美夢,但他們並沒想到,那些顧問把高額佣金放進口袋後,隨時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這一切現象底下,潛藏著一個根本的問題:究竟金融產業的產出該怎麼評估才合理?尤其是在金融從業人員個個荷包滿滿,但大眾財富卻崩潰的情況下?
衡量產出的方法之一是將所有投入成本全部加起來,包括代表人員成本的薪資支出以及代表資金成本的利潤水準等。然而,這個方法有兩個問題。首先,在一個非充分競爭的市場,最後的產出價值有可能被薪資和利潤數值誇大,因為參與者只要從事尋租行為(rent-seeking。譯註:又稱競租)就能輕鬆達到目的。第二個問題是,儘管今天所有人都已知道投入成本是多少,但金融產業的最終「產出」卻要很多年以後才會揭曉,甚至永遠也無法得知。即便金融部門的任務是要長期有效分配資源─即滿足儲蓄者和投資人的利益,但我們也要到明天才會知道今天的投資決策是否能成功。而且,如果決策不成功,也不盡然全是金融體系的錯。
另一個評估方法─這是目前建立國家帳(national accounts)的慣例─是將銀行業透過無風險利率(高信用度銀行業者的集資成本)和它們對顧客的放款利率之間的利差所賺到的收益,視為承擔風險的報酬。利差愈大,銀行服務的想像價值就愈高。然而,在金融危機過後,這個評估方式看起來又非常怪,因為承擔較高風險的銀行雖然的確促使當年的國民所得增加,但事後來看,它們卻也是導致後來國民所得崩潰的元兇之一。
實際上,金融體系的價格信仰─以及對這些信仰的信仰─絕對不是真理。網路泡沫不僅反映出金融中介人員的醜惡(當然,多半還是反映其醜惡),還反映出一個真心但錯誤的信仰:新科技將能改造經濟體系,並讓投資這些科技的人變得極端富有。
要判斷金融智慧是否真的有價值,必須觀察它最終是否讓生活水準提高,至少從社會的觀點而言是如此。遺憾的是,這個標準當然非常難以評斷。「咆哮的二○年代」最後雖被大蕭條的傷口取代,但我們確實也透過那幾年的繁榮,得到了大量生產的技術、福特的T型車(Model T)、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美國無線電勝利公司(RCA Victor)的留聲機和黑膠唱片(一九三○年時)、航空公司的誕生,和其他許許多多形塑二十世紀人類生活特色的事物。而二十一世紀初的金融全球化,確實也讓全球經濟得以實現一九六○年代以來最強盛的成長,因此而擺脫貧窮的人口數更是遠比以前多很多。然而,到最後,金融失敗的代價卻不成比例地落在西方國家納稅人的肩上。時間(從一九二○年一直到二十世紀下半段)和空間(從已開發國家經濟停滯到新興國家的高速成長)的不同情況,讓我們更難以論斷金融體系的成敗。若以這個方式來看,金融崩潰的問題在於,在金融擴張早期受惠的人─銀行業者和數億個因全球化而擺脫貧窮的人─並沒有在問題爆發後出面承擔那些代價:這些代價全都直接落在不見得有得到利益的西方納稅人身上。
在每一個經濟快速變遷時期,金融風險都會明顯上升。從英國一八四○年代的鐵路革命,到一九九○年代的資訊科技革命,每個重大的經濟轉型期,都伴隨著極不尋常的金融動盪。人們在這些過程中賺到了財富,但旋即失去,在這當中,贏家和輸家的產生幾乎完全隨機。儘管如此,人類卻還是寧願相信能控制自己的經濟命運,而且誤以為自己清楚知道誰應該為問題負責。因此,賺走大量財富的金融體系從業人員,自然就成了眾矢之的。但造就他們成為富裕贏家的,其實是整個社會追逐金融夢(不管這些夢是否踏實)的欲望。而當那些美夢變成夢魘,整個社會當然也就充斥不信任的氛圍。問題是,那種彼此不信任的心態會不會進而摧毀「成也它,敗也它」的創新文化(儘管這種文化是造成金融泡沫及所得分配極端不均的原因之一,但卻也是讓多數人,而非少數人生活水準提高的原因)?
第二個斷裂:世代間的矛盾
所得分配不均也許是擄獲最多新聞頭條的議題,這多半是拜「占領」行動所賜,不論是占領華爾街、占領舊金山聯邦準備銀行,還是倫敦聖保羅大教堂外的露營區。然而,第二個斷裂最後可能造成更大的問題,因為我們的民主基礎架構非常難以解決這個問題:各世代之間的戰爭即將爆發。經濟停滯導致嬰兒潮世代和較年輕世代的期望無法同時滿足,前者希望能享受健康且沒有財務壓力的退休生活,但錢從哪裡來?他們期待後代子孫能幫他們埋單。
現在,到處都能聽到人口老化相關的辯論。世界各地的老年人口依賴比─老年人相對工作年齡人口的比率─都即將上升,但已開發西方國家的情況特別嚴重。如果只看老年人口依賴比,德國、日本和義大利面臨的挑戰比法國、西班牙、英國和美國還要大。到二○三○年時,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會是老年人口(包括已退休與未退休),但其他四個國家的老年人口比率將大約只有四分之一。
近年來,因金融資產報酬率惡化(早在從金融危機爆發前,這個問題就已存在很久)和金融危機後經濟活動水準遠低於期望值的雙重打擊,人口老化的種種挑戰已變得更加嚴峻。在這兩個因素的綜合衝擊之下,西方世界似乎正快速走向一個跨世代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
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規定,基金經理人必須根據各種金融資產組合(主要是債券、股票和房地產,也就是英國典型退休基金或保險公司賴以維生的收入來源)的期望報酬,為顧客提供中期至長期的可能累積利益預估值。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還具體指定典型金融資產組合的低、中、高名目年報酬率。二○一二年時,享受有利租稅待遇的產品─多半是退休基金─的低、中、高報酬率分別是五%、七%和九%。
退休基金通常會投資較多資金在股票型產品,投資到其他金融產品的比率則較低。這麼做很合理,因為長期來說,股票的報酬率比其他類別的資產高,而且,由於退休基金的投資期間較長,所以股票當然容易吸引退休基金的青睞。在整個二十世紀,股票的年度平均實質(經通貨膨脹調整)報酬率超過五%,以過去一百年間發生的種種動盪來說,這已經算很不錯的表現。如果將今日的通貨膨脹率(通常是一年二%)反映進去,那就是約當一年超過七%的名目報酬,正好大約和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的估計值相當。
然而,近幾年的報酬率卻遠低於上述數字。從二○○○年年初科技泡沫達到最高峰並破滅後,英國股票的平均年度名目總報酬率大約只有二.五%,這部分同時涵蓋了股利和資本增值。相較於監理機關和退休金產業業者當初假設的標準,這個數字實在低得可悲。
而且,計入通貨膨脹的影響並考量基金對顧客收取的費用後,很多案例的「實質」報酬率甚至是負數。相較之下,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的這個數字是一八%,所以,在那段時間,退休金個個好運連連。遺憾的是,在好光景時,這些基金本來就沒有盈餘,所以一旦時局變糟,很多計畫當然也就變得非常脆弱。負責監督英國退休金計畫體質的退休金保障基金(Pension Protection
Fund)在二○一二年六月時宣布,退休金「赤字」已上升到極不尋常的三千一百二十億英鎊,這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不足差額。
小心赤字缺口
當然,這不是英國特有的問題。舉個例子,美國個別的州也因龐大的退休金短絀而頭痛不已。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的一份報告(也是在二○一二年六月發布),在二○一○年會計年度,這些州的資產相對其公共部門退休福利負債的缺口高達一.三八兆美元,其中七千七百五十億美元屬於退休金承諾,而六千二百七十億美元屬於退休人士的醫療保健成本。
18
和英國一樣,美國近幾年的情況也急速惡化:在二○○○年時,美國原本有一半以上的州都擁有足夠財源來因應這些成本,但到二○一○年時,只剩威斯康辛州敢拍胸脯保證自己擁有足夠財源。在那一年,有三十四個州的退休金不足差額比率超過二○%。不意外的,很多表現不佳的州遂成為信評機關的砲轟對象,伊利諾州的信用評等在二○一二年八月被標準普爾公司調降,成為加州以外最低評等的州。很多悲觀論者甚至認為伊利諾州即將成為「下一個希臘」。
在大西洋兩岸的這兩個國家,公共部門員工的退休金也許並不算優渥,但他們的退休財富卻堪稱典型的鍍金產品。換言之,遇到金融危機或經濟停滯期時,公共部門員工的保障可能比民間部門高。不可否認的,改革確實在進行,但誠如英國審計署(Audit Commission)指出的,改革的速度很慢:
退休金計畫的法律基礎導致它們沒有太多方法可用來因應成本上升的壓力。民間部門雇主調整退休計畫福利的彈性比公共部門雇主大..民間部門雇主會考慮採取的行動包括:提高員工提撥金額、降低應計率(accrual rates)、降低年度退休金增加金額、停止對新成員提供確定提撥計畫,或停止對現有成員提供確定提撥計畫,惟保留到目前為止的應計退休金..但在公共部門,福利結構是由國家決定..。
換言之,儘管企業可以削減現有員工甚至過往員工的退休金福利,但公共部門卻很難做到這一點。除了法律的限制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這麼做在政治上很不得人心。所以,公共部門寧可以不變應萬變,最差不過就是像伊利諾州那樣─一旦外界注意到後,被狠狠調降評等罷了。儘管退休金財務前景黯淡,當局卻通常寧可選擇「家醜不外揚」。當年尼克.李森(Nick Leeson。譯註:導致英國霸菱銀行︹Barings Bank︺倒閉的交易員)正是用這個方法來因應他的財務厄運。
然而,這個問題的寓意卻令人十分煩惱。除非退休金福利透過諸如大幅提高退休年齡、降低退休人員所得,或提高員工提撥金額等方式來縮減,否則,到時候一定要有其他人出面為這些成本埋單,當然,倒楣的主要還是納稅人和接受公共服務的國民。換言之,要解決因資產報酬不佳而衍生的公共退休金短絀問題,就必須緊縮財政政策,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麼做卻會導致經濟體系的需求降低,經濟成長進一步下降,並進而讓資產報酬率不佳的情況惡性地延續下去。到時候,最明顯的輸家將是年輕人。他們的教育成本已經比上一代高,但接下來的人生卻還要繳納更多稅賦來為那些厚顏聲稱自己擁有國家有限資源支配權的人埋單,幫他們支付所謂的應享權益。
第三個斷裂:債權人和債務人愈來愈不互相信任
美國、英國和很多歐元區國家目前還面臨另一個共同的問題:它們的財政都已經快維持不下去了。這些國家的債務人都必須向國外的債權人尋求協助。而且,以每個案例來說,債權人收回資金的機會都不高,至少無法收回具經濟及財務意義的錢。
美國及英國和南歐國家(如果經濟成長一直無法恢復,它們最終可能不得不違約)不一樣,這兩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印鈔廠,所以,它們的中央銀行可以藉由印鈔票來降低政府債券的殖利率,也可以藉此促使本國匯率貶值。當然,匯率貶值不可能沒有代價,誠如英國在二○○九年及二○一○年發現的,弱勢貨幣會導致進口成本上升,進而使家庭變得更貧窮。然而,這麼做也是一種「隱性違約」(default by stealth)的手段。如果外國人以某國的貨幣(而非其本國貨幣)借錢給它,又如果這個國家的貨幣大幅貶值,外國債權人就會發生損失,因為若以外國人的本國貨幣計算,他們購買的該國資產已經貶值。
舉個例子,想像一下,若美元因聯準會持續濫用印鈔的手段而相對中國人民幣大幅貶值,那麼以人民幣計算,中國先前購買的一.二兆美元國庫券的價值就會縮水。另一方面,理論上來說,更有競爭力的美元(譯註:指弱勢美元)應該能促使美國出口成長,通貨膨脹上升,進而使美國國民所得的名目價值提高。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美國政府負債占GDP比率將會因此降低。到時候,中國的損失將成為美國的利益,國內選民的利益將凌駕在外國債權人的利益之上。
這個動機不一致的現象導因於經濟疲弱,但更重要的是,它還可能反過來導致經濟疲弱的現象永遠延續下去,當然,一切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彼此的信任。債臺高築的民主國家選民有說不完的誘因來迴避撙節政策的施行,他們可以將負擔轉移給下一代,也可以將調整的痛苦轉移給外國人,畢竟外國人沒有選票。
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外國人根本不太需要煩惱這些問題,因為當時生活水準持續上升,而且每次經濟衰退後,也都能順利回升,國內選民及外國債券人也因此皆大歡喜。然而,在這個後危機時代,一個等同於長幼尊卑的秩序似乎愈來愈可能形成。擁有選票的國內債務人的利益當然會凌駕在外國債權人的利益之上。換言之,全球資金流動的泛政治化似乎已在所難免。
到時候,這個問題將以很多不同的面貌呈現。擔心無法回收資金的債權人將傾向於把錢存在本國。原本可能流入較具成長潛力的外國風險事業的錢,也可能被藏在床墊下,因為此時債權人認為安全性考量重於風險。到時候,全球失衡確實會縮小,但那只是因為外國投資人不打算繼續借錢給別國的人。一旦走到這個境地,信用緊縮將成為跨國的事件,想借錢的人將不得不開始在國內尋找資金。而一旦發生資金短缺的情況,金融機構也將難以逃脫被牽連的命運,因為它們將無法像金融危機爆發前那樣,在國際上募集很多資金,但另一方面,它們卻還是得承受在國內放款的壓力,而且可能還會被迫放款給看起來符合政治私利,但卻沒有經濟或金融價值的專案。而由於國與國之間彼此不信任,本國偏差(home bias)的傾向將逐漸形成,這又會導致股東、債券持有人、退休金和投保人等的利益遭到連累。
這時,還打算投資海外的人將愈來愈傾向於尋找不可能輕易因印鈔手段而「貶值」的產品。換言之,這些資金將加碼投資會因美元貶值而漲價(以美元計算的價格)的原物料商品和跨國企業。那又進一步意味,債務國除了拍賣傳家寶來籌錢以外,將愈來愈沒有其他選擇。即使量化寬鬆操作能鼓勵趨避風險的國內投資人持有更多本國政府債券,但這些債券的增值空間卻會因各國央行的作為而受限;另外,外國投資人則將愈來愈傾向於持有高生產力的資產。目前這個跡象已經非常明顯,有愈來愈多倫敦和曼哈頓的房地產落入俄羅斯、中國和沙烏地阿拉伯人手裡,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國內買家常因開價較低而被外國人排擠在市場之外。並且,有愈來愈多歐洲和美國企業被中國及印度的同業收購,而它們的目的通常是想要取得優勢科技。
在此同時,隨著國與國之間的信任感降低,各國將企圖強迫別國接受本國的意願,甚至改寫國際上的遊戲規則,朝對自身有利的方向走。美國監理機關干預美元交易的情況已愈來愈明顯,它們威脅撤銷在美國境外協助顧客從事不當美元交易的美國機構的銀行執照。針對不受美國司法管轄權規範的跨國美元金融活動設定這種非明文限制,最後可能反而會催生出其他足以和美元抗衡的準備貨幣。例如,有可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且在外交政策上向來對其他體制的行為漠不關心的中國一旦解除本國資本市場的管制,人民幣就有可能成為足以和美元抗衡的主要國際貨幣。正當西方債務人和債權人還忙著爭論誰應該為金融危機埋單之際,世界經濟及金融市場的重心有可能朝東方及南方偏移,西方的支配地位將也就此喪失。
接下來該怎麼做?
沒有了信任,各經濟體似乎很難重新回到先前的平衡及穩定。不過,目前彼此不信任的情況確實相當嚴重。銀行業已經不受外界信任,就某些案例來說,它們其實是自作自受,但現在連金融體系內的人也不再彼此信任。另外,一般大眾也愈來愈懷疑政治人物,他們貪贓枉法的野心確實很難讓人迅速恢復對他們的信賴。國內債務人不再受外國債權人信任。連中央銀行官員的崇高地位都大受打擊,因為他們創造愈來愈多的想像貨幣─不斷印鈔。
目前市場早已無法正常運作,但擁有重建市場能力的人不是不被信任,就是因為這個世界變得愈來愈全球化而失去重建市場的能力。這已不只是靠市場派(主張當前困境只是因為動物本能暫時崩潰,未來將自動復元)或政府主導派(主張採取明快的補救政策來重建經濟穩定感)的辯論就能解決的問題,取而代之的,現在我們應該做的,是要商討如何共同找出一個不寅吃卯糧、不要再對自己開一大堆無法兌現的支票的方法。我們必須共同找出一種足以提升彼此信任的方式,降低集體應享權益,進而終結經濟停滯的厄運。(本文選自第五章,陳若雲整理)
作者︰史帝芬‧金恩(Stephen D. King)
匯豐控股(HSBC)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兼經濟與資產分配研究中心全球主席,也是英國政府亞洲工作小組的成員,經常在《金融時報》與《泰晤士報》發表文章。目前與家人住在倫敦,閒暇時間彈鋼琴自娛。
匯豐控股(HSBC)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兼經濟與資產分配研究中心全球主席,也是英國政府亞洲工作小組的成員,經常在《金融時報》與《泰晤士報》發表文章。目前與家人住在倫敦,閒暇時間彈鋼琴自娛。
出版:商周出版(2013年9月)
書名:經濟成長的終結

目錄:
推薦序 經濟成長已將終結,該如何是好? 吳惠林
謝辭
前言 富裕年代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章 我們錯將進步視為理所當然
我們認為經濟衰退都是週期循環的,總會在逆境中反彈回升。不過,不是永遠這樣的。
第二章 停滯的痛苦
人類不喜歡失去已經擁有的。在經濟停滯時,不僅缺乏進步,更糟的是要抗拒經濟上的掠奪。
第三章 修復凋敝的經濟
利率下調、刺激方案與量化寬鬆似乎都沒有效,提振經濟的政策只會延長痛苦的停滯。
第四章 刺激方案是會上癮的止痛藥
我們希望貨幣與財政的藥方可以救我們,但持續使用這些止痛藥可能會產生不良的副作用。
第五章 刺激方案的限制:歷史的教訓
一九二○與三○年代的經驗告訴我們,刺激方案的效果總是有限,甚至可能造成新問題。
第六章 失去信任,也失去成長
信任不僅能提升經濟效率,更是社會體系很重要的潤滑劑。沒有信任,經濟很難復元,人類的互動也將逐漸毀壞。
第七章 三大斷裂
一旦經濟陷入停滯,這三個斷裂就會被凸顯出來:富人與窮人、老年人與年輕人、債務人與債權人。
第八章 從經濟失望到政治動盪
不願正視並著手解決因經濟失敗而衍生的困難,最後只會讓政治朝民粹主義及保護主義傾斜。
第九章 一塌糊塗的反烏托邦
十四世紀的英國,從黑死病爆發到農民起義的這段期間,發生了很多值得現代人記取的教誨。
第十章 如何避免成為反烏托邦
我們不能假裝只要一點點額外的量化寬鬆,或額外增加一些政府支出,就能解決當前的經濟困難。我的建議說來簡單,卻難做到。
註釋
參考書目
謝辭
前言 富裕年代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章 我們錯將進步視為理所當然
我們認為經濟衰退都是週期循環的,總會在逆境中反彈回升。不過,不是永遠這樣的。
第二章 停滯的痛苦
人類不喜歡失去已經擁有的。在經濟停滯時,不僅缺乏進步,更糟的是要抗拒經濟上的掠奪。
第三章 修復凋敝的經濟
利率下調、刺激方案與量化寬鬆似乎都沒有效,提振經濟的政策只會延長痛苦的停滯。
第四章 刺激方案是會上癮的止痛藥
我們希望貨幣與財政的藥方可以救我們,但持續使用這些止痛藥可能會產生不良的副作用。
第五章 刺激方案的限制:歷史的教訓
一九二○與三○年代的經驗告訴我們,刺激方案的效果總是有限,甚至可能造成新問題。
第六章 失去信任,也失去成長
信任不僅能提升經濟效率,更是社會體系很重要的潤滑劑。沒有信任,經濟很難復元,人類的互動也將逐漸毀壞。
第七章 三大斷裂
一旦經濟陷入停滯,這三個斷裂就會被凸顯出來:富人與窮人、老年人與年輕人、債務人與債權人。
第八章 從經濟失望到政治動盪
不願正視並著手解決因經濟失敗而衍生的困難,最後只會讓政治朝民粹主義及保護主義傾斜。
第九章 一塌糊塗的反烏托邦
十四世紀的英國,從黑死病爆發到農民起義的這段期間,發生了很多值得現代人記取的教誨。
第十章 如何避免成為反烏托邦
我們不能假裝只要一點點額外的量化寬鬆,或額外增加一些政府支出,就能解決當前的經濟困難。我的建議說來簡單,卻難做到。
註釋
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