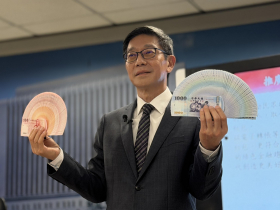中年失業的六年級生、放棄高薪外商工作的七年級生和曾參與新創遊戲開發的八年級生。
跨世代的組合,靠著一款主打台灣元素的恐怖遊戲《返校》,重新擦亮「台灣」這個品牌。
一月十三日,赤燭在這裡點了一支香,透過網路直播。香燒完的那一刻,《返校》在全球超過一億電腦遊戲玩家的平台Steam開賣。從那一刻起,赤燭在台灣及全世界,點了一把火。
《返校》這款恐怖冒險解謎遊戲,故事背景設定在六○年代戒嚴時期的台灣,意外挑動了台灣敏感的歷史神經,不但攻占媒體版面,更釀起政治風暴。民進黨立委陳其邁還在臉書上以《返校》中白色恐怖為例,要求政府轉型正義應加快腳步。
中國也瘋玩《返校》
恐怖電玩《返校》熱潮延燒到對岸,中國實況主「半支菸」還在直播遊戲時哽咽說出:「人不是該生而自由嗎?」


取材白色恐怖》台味驚豔國際 銷量衝第三
更令人意外的是,遊戲中灌滿台灣文化特有的音樂、場景、民間故事,搭配上懸疑、具壓迫感的劇情,對於不熟悉台灣歷史的國外玩家,照樣有吸引力。短短三天,登上Steam全球銷售排行榜第三名,打敗許多國際知名遊戲。而根據赤燭的數據,台灣只占營收的五六%,中國二三%,剩下二一%都是英文市場。
「很意外,真的很意外。」《返校》遊戲製作人、赤燭遊戲的共同創辦人姚舜庭接受《今周刊》專訪時說。
從國內外排山倒海而來的熱潮,對於這個才成立兩年、沒沒無名的小團隊,如同奇蹟。赤燭的六名創辦人,平均年齡不到三十歲,在因緣際會下四拼八湊,卻意外組成天衣無縫的團隊,一起走過峰迴路轉的開發過程。
這一切,要從二○一四年開始說起。那一年,姚舜庭失業了。
今年三十七歲的姚舜庭,在多媒體領域累積了近十年的美術和互動專案經歷,當時靠著在家接外包為生,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每天的樂趣就是玩桌遊,他自嘲:「那時就沒工作,從桌遊店走出來,都覺得自己很廢!」就在人生的最低潮,姚舜庭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地嘗試自己做遊戲。
「很多人都說我們故意挑敏感的白色恐怖當背景,但其實我一開始想講的故事,就是歐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姚舜庭說。他起初把遊戲取名《魔都》,從陰森森的小遊戲開始,講述著極權社會下的小人物故事,姚舜庭愈做愈起勁,套入了各種遊戲要素。開發半年後,他才發現格局太大,難以完成。
姚舜庭便將場景從「都城」收斂到「學校」,就這樣埋頭做了一年,姚舜庭看著有限的存款,「覺得該面對現實,考慮回職場。」一五年一月,他偶然在臉書和朋友聊天,過程中姚舜庭提到他在做的半成品遊戲,隨手將遊戲截圖傳過去。這幾張圖,得到了改變他人生的回答。
「我很喜歡你的風格。」「真的?」「配合台灣的校園鬼故事,感覺可以做一個作品。」
姚舜庭聊天的對象,是還在念碩士的王瀚宇。王瀚宇和哥哥王光昊,本來就是「腦洞工作室」共同創辦人,和鈊象電子合作過,已是小有成就的遊戲製作人。「當時看到覺得很屌!」王瀚宇回憶:「就是你不用說你的設定,一個畫面就能夠表達這是個恐怖的東西,且是台灣元素的故事,很厲害!」
兩兄弟和姚舜庭在麻辣鍋店見面,一拍即合;姚舜庭也受到他們的鼓勵,才認真組成開發團隊,著手製作《返校》。隨著成員企畫江東昱、美術陳敬恆陸續加入,團隊實力愈來愈強。但此時還沒有成立公司,一群人常在咖啡廳裡吵成一團,直到第六個團隊成員出現。

資本額僅百萬》邊接案邊開發 不支薪苦撐
他是楊適維,今年三十一歲,帶著一點ABC的氣質,與赤燭的其他人完全不同。楊適維在高中玩團、大學在美國念書,畢業後到廣州就業,回台後在三菱東京日聯銀行,擔任儲備幹部。看似一帆風順,楊適維卻感到空虛,覺得人生缺乏挑戰。
有一天,他無意間和高中同學,正好就是赤燭的王光昊在網路上聯絡,知道王氏兄弟在做遊戲,「每次和他聊天,都覺得他的人生比我精采太多了!」楊適維說。王光昊的投入和熱情,是楊適維在金融業找不到的,他便開始自學程式設計,最後也放棄外商高薪,透過介紹加入赤燭團隊。
財金背景的楊適維說:「我進來第二天,他們就為了劇本吵架,我才發現,這些人真的沒有商業概念,很生氣地說:『為何你們沒有製作人?』」楊適維便幫六人設立公司、分配股份,「那時大家都窮,資本額就設在一百萬元,六人均分股份。」
一五年九月,從一個人到六個人,赤燭終於成形。然而,真正的挑戰還在後面。
「我們公司資金缺口永遠都是一個月以上,連台大育成中心都是勉強住進來。」楊適維笑著說。不但姚舜庭當時連十七萬元的入股錢都拿不出來,還得借錢籌資;成員陳敬恆也因孩子甫出生,經濟壓力增大,「所以大家都很惶恐。」只能一面開發、一面接著外包案子養活自己。
楊適維說,當時過著「星期一到五做《返校》;六、日接案子」沒日沒夜的生活,完全沒有休息時間。獨立遊戲開發者分享會共同發起人林容生,與團隊熟識已久,他透露在最緊急的時候:「他們也停止六位創辦人的支薪,繼續自己墊錢進公司。」一路撐下去。
《返校》像一個黑洞,不斷吃光六個人的錢;而開發過程裡,也前後歷經五次「砍掉重做」的痛苦過程。王瀚宇說,「有時要把程式修改到好比重新做更累,就全部重寫。」最後一次在一六年一月,儘管距離《返校》要公開展示試玩版前,僅剩不到兩個月,團隊突然覺得許多細節不到位,就大刀闊斧砍掉了已花四、五個月時間再製的版本,一切又得歸零。
不過,就在團隊最絕望的時候,林容生卻帶來了天使。原來,林容生與台灣獨立遊戲界的人士,在一六年初正準備成立一筆資金,幫助台灣的遊戲開發者。「我們的合夥人都想尋找台灣適合的團隊與標的,最後覺得在那個時間點最適合的就是赤燭跟《返校》。」林容生說。
林容生觀察,比起不少小型團隊,赤燭團隊的能力相當全面,在設計、音樂音效、美術、文本等都展現水準,因此雀屏中選。赤燭終於不再是自己苦撐,得到林容生和合夥人資金上的幫助;而《返校》的遊戲內容也「愈砍愈好」,終於獲得資深玩家的青睞,成為獨立遊戲界的話題。
上架後,《返校》話題發酵,不僅衝上Steam平台排行榜,也意外占據了媒體版面。團隊承認,《返校》題材帶著爭議性,讓很多平常非遊戲玩家的人買單,「但那不是我們的初衷。」姚舜庭說。
在國際已是知名遊戲製作公司的雷亞遊戲總監李勇霆觀察:「選擇題材不受限,是獨立團隊的精神所在,即使被部分人士用政治議題去刻意包裝,但團隊的初衷,應該還是說一段有意義的故事。」《返校》扎實的遊戲內容,掌握了好玩、好看及好聽,也因此連不熟台灣歷史的國外玩家都被吸引。

▲製作團隊要求完美,曾因細節不到位,前後砍掉五次內容,歸零重製。(攝影/唐紹航)
暴紅後下一步》堅持獨立精神 拚叫好叫座
暴紅後,赤燭團隊的擔憂卻消散不去。除了擔心外界對遊戲本身的關注受話題操作而失焦,楊適維也表示,他們仍怕「很可能下一款遊戲賣不好,就跌倒了。」雖然遊戲銷量非官方統計超過四萬套,但赤燭至今還虧損,資本額仍是一百萬元。
如同《返校》要傳達打破極權體制的精神,讓許多人回想到台灣戒嚴時代、追求自由的歷史一樣,他們首款獨立遊戲一反常態地搶進一般大眾視野,為獨立遊戲發展的局限打開一道缺口。有了赤燭,或許我們能期待更多的台灣內容,透過成熟的表現方式,進軍國際。
「赤燭」神祕推手林容生
——以台版Indie Fund,逆轉開發環境劣勢
「個人觀察獨立遊戲開發數年下來,看赤燭團隊本身的構成,比起不少小型團隊來說,能力其實算相當全面。但在開發關鍵期遇到的資金缺口,在台灣並沒有適合的解決方案。
不過,2013年時資策會主辦、我們協辦的「台北遊戲開發者論壇」曾經邀請美國 Indie Fund 的一位合夥人來台灣演講,講解他們以「混和式貸款 (Hybrid Loan)」來實行獨立開發者之間互助的模式。在那之後這件事我就一直放在心底,但幾年下來找不到適合的時機。
直到2016年初,我遇到另一位合夥人,他也很想尋找台灣適合的團隊與標的。最後覺得在那個時間點,最適合的就是赤燭和《返校》,於是也找了其他的夥伴,有了適當的合夥人與標的後,我們才開始在台灣嘗試美國的Indie Fund模式。
我不知道這樣對於改善台灣投資環境幫助會有多大,我覺得真正的關鍵,還是在團隊自己否能瞭解自己的優劣勢,並好好運用自己手邊能運用的資源。赤燭除了堅持品質之外,也把資源花在正確的方向。沒有這些,再多的資金協助,也幫不上忙。」
(林容生口述;楊卓翰整理)
赤燭遊戲
成立:2015年9月
成員:8人,平均年齡30歲
資本額:100萬元
成績單:首款遊戲《返校》推出一周下載量破3萬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