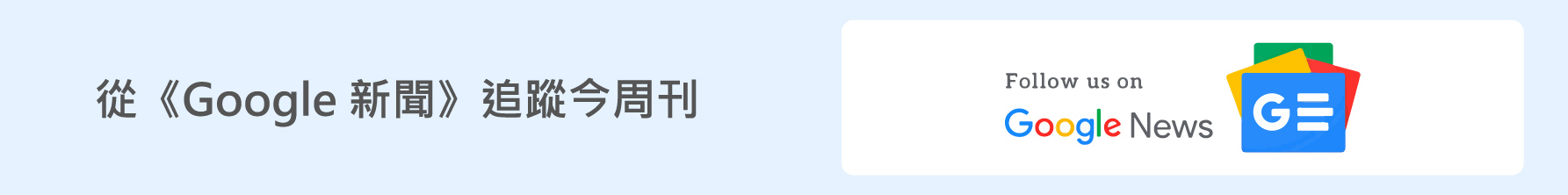我望著窗外,回顧我可悲的一生。我在小聯盟裡翻不了身,我的職棒生涯是一串漫長的失望。我是個兒時被性侵,無力面對創傷的男人。我極欲埋藏往日的真相,卻找不到足以封埋過去的深洞......我的自尊心低到無法度量,上帝賜予我健康身體和聰敏的頭腦,以及一個美麗的家庭,但我卻把自己的人生,變成無藥可救的難題......
遊騎兵覺得失去我也不會有什麼損失,因為──憑心而論──一個三十一歲、剛被敲出六支全壘打的蝴蝶球投手,有何市場可言?
遊騎兵是對的,沒有半支大聯盟球隊會對我有興趣,因此我只能繼續留在紅鷹隊効勞,直接進入先發輪值,被打到滿頭包。我曾在連續二十三局中,被轟出八支全壘打,在先發的前八戰,交出二勝五負的戰績,自責分率高達7.00。由於肩膀傷痛,決定休息一陣子,有幾週被列入傷兵名單。等我歸隊時,投球狀況僅只好一點點。我不斷提醒自己,我仍是個蝴蝶球的新手,但還是忍不住懷疑未來的方向──和未來的人生。
改投蝴蝶球原本想大破大立,而非一敗塗地。我有好多的疑問,滿腹的焦慮,而棒球只不過是其中最輕微的一項。
那年夏天,安妮懷了老三,那應該是喜事,因為兩個女兒健康活潑,老三又即將來報到,但事實卻非如此。其中一個問題是,我快被錢逼瘋了,我們剛在納許維爾買了房子,安妮和孩子住在那兒,所以我們可以省下在奧克拉荷馬市租屋的錢。我又回到遊牧歲月了,我在一位牧師朋友家打尖,或花七十塊一晚,住紅屋客棧(Red Roof Inn)、伊克諾旅店(Econo Lodge)。出城比賽時,我便辦理退房,把細軟拖到會館裡暫放,等回來後再把東西拖回旅館。我花很多時間檢視銀行帳戶、信用卡帳單、房貸付款,努力平衡各項支出。我們雖然不至破產,但在財務上也看不到明天。我生於寒微,習慣沒錢的人,會想要捉住每一分錢。買冷氣機時,為了省五十塊美金,我會到網上搜尋半天。如果要我在名牌和廉價品間做選擇,我當然是選擇廉價品。但安妮成長於納許維爾的望族,家中從不缺錢。
你猜我們婚姻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提示:和我的球種無關。
那年夏天,安妮有天到跳蚤市場,想找個飾品放到新房前陽台上。她發現幾個漂亮的陶甕,一般店裡一個大概要價三百美金,但在跳蚤市場,一對只要一百塊。她知道我在為錢傷神,所以辛辛苦苦才找到這種好價錢,想美化我們的房子。她打電話和我商量。當時我住在美國中部一間飯店裡,我立刻走出房間到走廊上;因為我不想在室友面前跟老婆爭執。
我們要陶甕做什麼?除了讓前陽台變得更雜亂,有什麼意義?我說。
我真的很喜歡它們,R.A.,擺在門前會很漂亮,真的很搭,而且和店裡的價錢比起來,一點也不貴。
我才不管它們在店裡值多少錢,一百塊就是一百塊。我們不是富貴人家,沒有陶甕日子也能照過,不是嗎?
我才不管它們在店裡值多少錢,一百塊就是一百塊。我們不是富貴人家,沒有陶甕日子也能照過,不是嗎?
我像個控制狂般地不斷遊說,混蛋極了。安妮不但沒亂花錢,還精打細算,她想把新家佈置得美觀,我卻不斷嚴厲批評,扯她後腿。
我說,好吧,要買就買,但下次妳的支票跳票,可別跟我抱怨。安妮把陶甕買下來了,大家都說漂亮。陶甕在一個月後被偷走了。
就連這樣一件小事,也會造成夫妻口角。
我夾在日益累積的財務與職場壓力間,好比《星際大戰》第四集中,掉入垃圾壓縮器裡的天行者路克、楚霸客(Chewbacca)、韓.蘇羅(Han Solo)及莉亞公主(Princess Leia),覺得牆壁從四面八方擠來,將垃圾推到我面前。真的就是那種感覺。
因為我自慚形穢,我在許多球季中,自覺像個垃圾,一個超級大垃圾。
我偏離了正道。
違背了對安妮和上帝的誓言,變成了自己最不想當的人:一個捻花惹草的球員。我不是慣犯,也不至滿城劈腿,但重點不在於次數,而在於信任的破滅。
我望著鏡子,痛恨鏡中的我,討厭自己的改變。我與安妮之間有道鴻溝,與自己也有隔閡,更覺得自己是個表裡不一的騙子。我感到恐懼,心情沉重,那些感覺撼動了我搖搖欲墜的信仰,我只能故態復萌地去因應,逃避。我逃得遠遠地,我埋頭看書,躲進電影院裡,坐在後排吃爆米花。棒球是我的謀生工具,也是我的逃避工具。在棒球的世界裡,你可以當個永遠長不大的青少年,所有需求和反覆的脾氣,都會有人打理;自戀的球員,多如葵花子。這樣的生活,對家庭生活之不利,遠超乎你能想像。外人以為職業球員的生活光鮮多金,卻看不到球員妻兒承受的家庭失能與沉重壓力。春訓時一離家就是六個星期,接下來的六個月,則是進進出出無法久留。在所有的英文字彙中,你最常用的字就是「再見」。即使努力想作個盡責的男人,還是免不了缺席一些活動,一些極為重要的活動。
我們女兒萊拉(Lila)出生時,你猜我在哪兒?我在達拉斯-沃斯堡國際機場(Dallas-Fort Worth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快餐店裡,等著轉機回家。
兒子以利亞(Elijah)出生時,你知道我在哪兒嗎?在德州圓石(Round Rock)客場的會館裡等著先發上陣,安妮正在生產,我岳母拿著電話讓我聽。(二○○六年時,小聯盟還沒有所謂的陪產假。)
離家時間那麼長,每次回家,都像在壓力鍋中進行對話,討論著汽車換輪胎、孩子耳朵感染、手機費爆漲等問題。
如果你有一點點的自覺,便會知道夫妻間的責任分配極不平均。你的太太要帶孩子看兒科、打電話找水電工、和老師會面,而你只需要在牛棚裡勤練蝴蝶球握法就成了。
你的妻子要給孩子講睡前故事、確認衣櫃裡沒有怪物、一大早得起床載孩子上學;而你在賽後和朋友歡聚,第二天睡到十一點才起床。請別誤會,我真的很努力練球。每次有機會到大聯盟登板,都會力求表現。我熱愛我的工作,也很感激有機會打職棒。但老實說,職棒的最高層級根本是個異想世界,聽到的盡是阿諛與吹捧,出門遠行有專機伺候,住每晚三百五十美元的飯店,彷彿全世界都在告訴你,而且是堂而皇之地讓你知道:你是多麼、多麼的特別。
但我心底知道,自己並不比上帝其他子民特別。我知道會館裡的工讀生、停車場的管理員,在宇宙中與我同等,甚至比我更重要。或許他們更加盡善地改變世界,幫助他人;或許他們更忠於自己的信仰,而我只是個虛有其表,球路飄忽的人罷了。二○○六年夏天,這種不踏實的虛假感,淹沒了我整個人生。
我在各方面都覺得徹底失敗:在信仰上,尤其是在作為安妮的丈夫和終身伴侶的角色上。我未能照顧她的需求──給她應得的待遇。我理想中的好丈夫是鍾愛、善良、耐性而忠誠的,能讓妻子感到獨一的尊寵,體貼又窩心。
但是我完全不懂得體貼安妮,而且不僅如此,我非常冷漠,吝於以行動表達愛意。我不習慣去牽她的手,或對她說我愛你,或送花讓她驚喜。
我逃避親密關係,視親密為畏途。我下意識地知道,這和我過去遭受性侵有關。我的生活經驗雖然造就了今日的我,但過去已矣,我理應活在當下。我什麼時候才能鼓起勇氣,面對此生一直在閃躲逃避的惡魔?我禁不住要想,如果安妮可以重來,一定不會嫁給我。我覺得好孤單,安妮也是。
有時我覺得你好像不愛我了。你愛我嗎?她問。
我當然愛妳。
可是你為什麼都沒表示呢?為什麼總是對我發脾氣、讓我傷心?為什麼你對孩子那麼溫柔慈愛,對我卻不一様?
小孩子不一樣,他們需要爸爸的關愛,他們需要被愛與安全感。
難道你不瞭解我也需要嗎?為什麼我總是排在最後一名?
妳不是最後一名。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對孩子表達愛比較容易。
為什麼比較容易?為什麼不能對我示愛?為什麼愛我就那麼難?
安妮說得當然一點都沒錯,我卻抵死不認,自我封閉,防衛心極強。我找盡藉口,我怪她及她的花錢習慣,也怨自己自責分率太差。總之千怪萬怨,就是不怪罪自己。有時我在大發雷霆後,又悔不當初;在欺騙和背叛安妮後,內心更是無地自容。
我在婚前告訴安妮,自己還是處男,其實不然。我從未告訴她,自己曾被性侵,而且在被性侵的那年夏天,便接觸到色情書刊。我從來沒告訴她,身體的接觸會讓我聯想到被性侵、欺凌及佔便宜。安妮有權知道一切,我卻因害怕失去她而隻字不提。
或許是因為罪惡和羞愧感太強,而讓我無從啟口?
因此我封閉自己,編造各種有失公允的藉口,安妮發現,她跟一名本意良善,卻用盡一切行動將她推開的的男人,綁在婚姻裡。
這個男人和其他遭受性侵的孩子一樣,深受煎熬且自慚形穢。
這一年我投得很不順手,婚姻關係更是江河日下。每次和安妮談話,我都希望能心平氣和,但我們多半開吵。
八月初某天下午,懷孕八個半月的安妮打電話到會館找我。以前她從來不曾,也不會打電話到會館。
我心中做了最壞的打算,該不會是哪個孩子出事了吧?
我們需要好好談談,你現在馬上就回來,安妮說。她的口氣十分歇斯底里。
發生什麼事了嗎?
現在就回來,她說。如果你還想要這個婚姻,現在就立刻回來。
我的喉嚨像塌陷了般,難以吞嚥。周遭的隊友正在準備上場比賽,我大概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罪有應得。
我告訴麥可.鮑藍傑,我要請三天事假。他看出我的神色有異,便說「去吧。」我搭清晨六點的班機回納許維爾,飛機下降時,我望向納許維爾的天際線,好害怕面對安妮。
我們的牧師卡特.昆蕭(Carter Crenshaw)到機場接我。
我一直為你和安妮祈禱,我唯一能說的是,你要對她完全坦白,卡特說。
安妮待在娘家,當我看到她時,她的眼睛紅腫,好似哭了許多天。我恨不得鑽到她爸爸書房的地毯下。書房的木頭裝潢看起來仍有三尺厚,我則自覺只有三吋高。
珍(Jen)也在場,她是安妮家的朋友及治療師,到場來支持協助我們溝通。
我要你把一切告訴我,安妮說。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該從何說起。安妮的痛苦是我造成的,我的罪惡感排山倒海而來。接下來兩個鐘頭,令我痛不欲生。離開家時,我毫無把握婚姻能否維續;不知將來自己會不會也變成那種只有在週二、週四和每隔一個週末,才能和孩子見面的父親。
此時我雖然無心棒球,卻不能放棄工作,我們需要這份薪水。在紅鷹隊打完這個球季後,戰績九勝八敗,自責分率4.92,差到會被球團釋出的程度。我對未來茫無所知,不清楚季後返家時,會不會成為單親父親。我在年底收拾行囊,進入職棒已十一個年頭了。我開車回納許維爾,從四十號公路的二○四號出口下來,直驅西區社區教會(West End Community Church),和安妮及卡特見面。我在停車場停妥車子,祈求上主垂憐,雖然我知道我並不值得祂憐惜。
谷底
一個人懷抱愧疚地獨處久了,便會鑽牛角尖,往死裡鑽。這就是我在九月底時的心情寫照。球季結束後,我回到納許維爾,住進舊家(我們還沒賣掉),安妮和孩子們搬到新家去了,因為安妮希望目前能這樣。
我不確定我還能相信你,她說,你跟我認為的那個人不同。
我並未試圖說服她,試了也沒用,這不是吵輸吵贏的問題,而是如何重獲她的信任。
修復破損的關係。在對婚姻背信之後,豈是易事。簡直難如登天。
你怎麼可以這樣?怎麼可以欺騙我,背叛我?安妮問。
她有權知道答案,有權知道更多。無論我說什麼,都無法表答愧疚於萬一。
我不怪妳生氣和覺得受背叛,因為我的確背叛了妳。我只能卑微地向妳認錯,懇求妳原諒。
假以時日,或許我會原諒妳,她說,但是我不知道得要多久。我好害怕,我以前是那麼地信任你,你知道我多麼相信,你是個忠實可靠的男人嗎?
我能對她說什麼?
我無話可說。
我甚至不知為何會出軌,那不是計劃中的事,我對對方毫無感情,只是一種逃避,不想有任何牽扯。 婚外情很快結束了,徒留打破婚姻誓約後的罪惡與愧疚,我每天都得面對盤繞不去的罪惡。
每天早上,我和卡特會面一個鐘頭,告訴他所有事情,坦誠每項過失。卡特對我相當寬容,卻不縱容,我也不希望他對我放任。
你必須挺住,忍受安妮的攻擊,不得反擊,他說。你必須對她和盤托出所有幹過的事。
我繼續挺住,並住在舊家。我走進黃色的前門,望著幾乎空無一物的客廳,倒在白底紅花的沙發上,試著入睡。白天,我去看安妮和孩子們;晚上,我回到舊家,幽暗孤獨的空屋與我的心情兩相呼應。安妮和我的關係很糟,她擔心我會開車載走孩子,甚至考慮要換門鎖。
我望著窗外,回顧我可悲的一生。
我在小聯盟裡翻不了身,我的職棒生涯是一串漫長的失望。
我是個兒時被性侵,無力面對創傷的男人。
我極欲埋藏往日的真相,卻找不到足以封埋過去的深洞。我是表裡不一的偽君子,表面佯裝成虔誠的基督徒,實際卻背叛了妻子和上帝。
我的自尊心低到無法度量,上帝賜予我健康的身體和聰敏的頭腦,以及一個美麗的家庭,但我卻把自己的人生,變成無藥可救的難題。
我躺在黑暗中祈求上帝幫助,卻又相當掙扎。
上帝為什麼要幫助我這種人?我心想。
因為上帝的慈愛無限,祂一定會原諒你,我提醒自己。
我在小聯盟裡翻不了身,我的職棒生涯是一串漫長的失望。
我是個兒時被性侵,無力面對創傷的男人。
我極欲埋藏往日的真相,卻找不到足以封埋過去的深洞。我是表裡不一的偽君子,表面佯裝成虔誠的基督徒,實際卻背叛了妻子和上帝。
我的自尊心低到無法度量,上帝賜予我健康的身體和聰敏的頭腦,以及一個美麗的家庭,但我卻把自己的人生,變成無藥可救的難題。
我躺在黑暗中祈求上帝幫助,卻又相當掙扎。
上帝為什麼要幫助我這種人?我心想。
因為上帝的慈愛無限,祂一定會原諒你,我提醒自己。
一天早上我在沙發上醒來,心情空前苦悶。我不知道是什麼引起的,但已無所謂了。
或許我該就此了結一切,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痛苦。
我尋思各種選項,一氧化碳?可能性頗高,我們剛蓋了一間新車庫,若是舊車庫的話,就太通風了。
刀子或槍?想都別想,我不喜歡刀刃或子彈。
再不然去加入陸軍,派到伊拉克作戰;或不繫安全帶製造高速車禍?那樣應該可以萬無一失了。
我胡思亂想各種可能,越想越煩亂,我懷疑自己會真的去做,因為我太害怕了,而且我很想重修舊好。我想要重新贏回安妮和她家人的信任,成為一個慈祥和藹的父親。我想將功贖過,祈求上帝的垂憐。我也想擁有健康的婚姻關係,做個身心自在的人。問題是我過於自責,心裡總有個負面的聲音:
所有你曾經愛過、在意的事都被你搞砸了,你對妻子做出最殘酷的事,你根本表裡不一到了極點。
這個惡毒的聲音很具說服力,因為它的責難都是鐵錚錚的事實。
人生還有什麼意義?何必再混下去?一了百了不是更省事?
我全力反擊,拒聽魔鬼的擺佈。我聽見聖靈的聲音:你不是輕言放棄的人,人生還有很多值得去過的事。你雖犯下大錯,傷害了別人,但你心中有主,上帝是愛你的。
你不能隨便一走了之,我告訴自己,難道你要教導孩子:遇到挫折,就自殺逃避嗎?
秋去冬來,自殺的念頭旋繞不去。前一天還很堅強,第二天又想出無痛的自殺新法,我的生命在這兩股矛盾的洪流間拉扯。我愈想到孩子失怙,便愈覺得自殺的念頭不可取。
幸好我又慢慢重拾決心了。
選擇希望,別選擇絕望。選擇希望,努力奮戰,要比在投手丘上或任何地方更奮力而為。為了上主、安妮、孩子和你自己,非振作不可──當個男子漢,重振自己的人生。雖然兩股聲音持續互相叫囂,讓我深受折磨,但我還是選擇了希望。
我將車子停到破辦公大樓的停車場裡,大樓位於納許維爾的綠丘區,旁邊是髮廊和藝廊。時為週五下午,我到此見一位叫史蒂芬.詹姆士(Stephen James)的人,他是朋友介紹的心理顧問及醫師。我搭著嘎吱作響的電梯來到三樓,心裡七上八下地走進他的辦公室。多年以來,我對心理諮商一直抱持成見:只有懦弱、迷失而找不到出路的人,才會去看心理醫師,而且專談些娘們的玩意。現在我自己成了迷失的人,我的成見也即將改觀。這裡是個可以告白私密的地方。我渴望援助,卻又不願敞開心扉接受幫忙。
史蒂芬的辦公室裡有兩張椅子、一張沙發和一個可以俯瞰露比餐廳(Ruby Tuesday)的窗戶。我和他面對面,已來不及找藉口開溜了。兩人相互握手後,我在椅子上坐定,狐疑地看著他。此人與我年紀相仿,一頭淡棕色頭髮,有對藍眼,舉止友善,可惜對我不管用。我善於拒人於千里之外,跟人保持安全的距離,我這輩子都在幹這檔事。史蒂芬望著我,看得出他在打量我,我穿著運動褲和一條破爛的T恤,不記得有沒有梳過頭髮。
我的蓬頭垢面,想必他都注意到了──怎麼可能沒注意到呢?──但他沒作任何表示。
史蒂芬說:告訴我,你為什麼到這裡。
我這陣子非常不順利,有人認為我應該來這裡談一談。
你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嗎?
他們很推薦你,我的心態很開放,試試也無妨。
史蒂芬點點頭,直視著我的眼睛,刻意讓沉默充盈房中。我們倆都知道,我並沒有真正回答他的問題,我猜他曉得我在胡扯,這令我非常不自在。每當我說話時,看得出他很仔細聆聽,心無旁鶩。
這也令我侷促不安。
幹嘛沒事停下來不講話?我們不能一直聊就好了嗎?我好想對他說。
史蒂芬提出很多問題。
你願意對自己,對我,完全開誠佈公嗎?
能不能把你的現狀告訴我?還有你此時的感受?
如果我們做諮商,你會願意堅持下去嗎?即使有時過程會很痛苦,挖掘出你築起心牆,隱藏多年的問題?
我告訴史蒂芬,我知道過程會很痛苦,其實我根本不懂。我不知自己有什麼問題,更不懂他所謂的「心牆」意指為何。我們第一次會面時,我幾乎像接受電視訪問般地迂迴閃躲他的問題,大打太極。
多年來,我已很擅長對外擺出與人為善的樣子,實則不允許任何人跨入我殘破的內心了。史蒂芬對我的外強中乾,完全了然於胸。
這傢伙裝真誠的能力,果真已臻化境了,史蒂芬對自己說。
和詹姆.史蒂芬會面的一整個鐘頭裡,我也在自問,這傢伙可靠嗎?我能和他分享我人生中最深沉黑暗──從來不曾與任何人分享過的祕密嗎?
他會對我不離不棄嗎?
即使坐在史蒂芬對面,我還是矛盾到不行。我很不想做心理治療,挖掘過去和所有的傷疤,但又厭倦了躲躲藏藏、話無半句真的歲月。我想獲得自由。
到底決定怎樣?我問自己。要繼續走在陰暗的途徑上,或去過上帝希望給你的豐富歡樂日子?
我和史蒂芬握手。
下星期見,我告訴他說。
整個冬天,我搭著咿咿呀呀的電梯到三樓,履行我答應史蒂芬做的功課。起初,我給他電視訪問式的制式回答,但史蒂芬都會當面點破。這是我這輩子幹過最困難的事,我把保姆的事告訴史蒂芬,跟他談學校裡的幹架、年少時的輕狂魯莽、空屋過夜的日子,以及對安妮隱瞞的祕密。我以為只要不斷前進,繼續保持先發投球,便能克服這一切。
我坦承自己在內疚與羞愧中度日,我相信人們若是知道了R.A.迪奇的真面目,便不想與他有所牽扯。
我告訴史蒂芬,現在他全都知道了,我很害怕他會跟許多人一樣,棄我而去。
事情不都一向如此嗎?人們離棄你?利用完你後,就揚長而去了?
我不會離棄你,R.A.,我答應你絕不會棄你於不顧,史蒂芬說。房裡一片死寂,他瞅住我的眼睛,我不想看他。史蒂芬說,看著我,仔細聽我說,R.A.:我絕對不會棄你於不顧。
我相信他,真的相信他。我想哭,我哭了一下下,但努力忍住了。
史蒂芬說,我真的替你感到好抱歉,好難過,我知道你一定很痛苦。
數週過去了,數個月也過去了,舊的傷疤逐漸癒合脫落,我覺得赤裸而脆弱,彷彿有人開著垃圾車,把所有垃圾全倒在前院草坪上。
該從哪裡開始清理?垃圾又該丟往何處?
我不知道,也毫無頭緒,但我曉得史蒂芬會從旁幫我找到方法。他是我第一位無條件信任──第一個可以分享一切的人。我在他嫻熟堅定的引導下,度過了人生最恐怖,也最重要的旅程。
即使在痛苦中,我仍知道這是我的福氣。
一整個冬天,我都在追尋真實的自我,接納事實。我努力與安妮和好,對著體育館牆壁苦練蝴蝶球,在史蒂芬面前坦露靈魂。密爾瓦基釀酒人(Milwaukee Brewers)的高德.艾許(Gord Ash)打電話來,邀我參加小聯盟訓練營,這是我唯一接到的邀請。道格.梅文離開遊騎兵後轉入釀酒人隊,艾許是他的副總經理。就算我無法加入釀酒人隊,他們農場最高等級的隊伍 就在納許維爾,換句話說,我可以持續接受史蒂芬的治療。
這種機率真的不高──唯一邀約的球團,其最高等級的農場隊,竟然就在你的家鄉。對正在為自己的靈魂奮戰的我,這是最棒的地方了。
感謝祢,上帝,感謝祢賜給我奇蹟,賜給我這個助我逆轉人生的好人。
我還有許多自修的功課要做,我發現檢視自我的坦實過程,並非井然有序或可以預期的。當我出發前往亞利桑那州參加春訓時,感到長久來不曾有過的希望,我幾乎把所有的祕密都告訴史蒂芬了。
我終於快要自由了。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德州阿靈頓,遊騎兵球場
計分牌上的時間顯示兩點零二分,我在客場的休息區裡,回憶如潮襲上心頭。精心剪修的球場上一片寧靜,這種打擊前的平靜,有種超現實的感覺。再度回到這個有過我最美好──及最糟糕回憶的場地,令我十分激動。我望著中外野區外的辦公室,想到一九九六年夏天,道格.梅文撤銷給我的八十一萬美元簽約金時的表情;我望著投手丘,那是我以蝴蝶球新秀之姿,被底特律老虎敲出六支全壘打,並列當代被轟出全壘打紀錄的地點。
也是在同一個投手丘上,我在二○○一年,投出初登大聯盟的首役,以及二年後上場救援,取得生涯首勝。這個球團,是我和安妮生下前三個小孩──葛碧兒、萊拉和以利亞──期間的歸宿,我有幸在此結交馬克.塔謝拉、麥可.楊、傑夫.布蘭特利、羅斯提.格里爾及傑.鮑威爾(Jay Powell)等英雄好漢。
我在這裡脫胎換骨──從傳統投手成為蝴蝶球投手──並在過程中,經歷情緒的擺盪與成敗的起落。
我在德州的歲月裡,曾短暫效力於強尼.歐茲及傑瑞.耐隆麾下,接著又投効於巴克.修瓦特,修瓦特是第一位真正願意給我機會的球團總教練。此外,並受惠於郝西瑟、馬克.康諾、魯迪.傑拉米洛(Rudy Jaramillo)、巴基.丹特(Bucky Dent)、李.唐諾及安迪.霍金斯等優秀教練的指導。
重返舊地點醒了我,人在現世必須不斷面對的一項挑戰:如何在痛苦與喜樂中,活出當下。能夠學習承擔苦樂,昂然行立於人世,是上帝賜給我,最真實的禮物之一。
我的一生並非總是順遂,卻十分富饒,這點令我滿懷感念。(本文選自第十三章,十四章陳若雲整理)
作者︰R.A.迪奇R.A. Dickey
曾獲選亞特蘭大奧運美國代表隊,職棒選秀第一輪就被德州遊騎兵隊選中,之後被檢查出右手肘缺乏尺側副韌帶,開始浮沉的職棒生涯。三十一歲才轉型為蝴蝶球投手,多年練習,總算站穩大聯盟。2010年至2012年為紐約大都會隊投手,2012年獲頒賽揚獎,同時是史上第一位以蝴蝶球投手身分獲得此殊榮者。目前效力於多倫多藍鳥隊。
威恩.考菲Wayne Coffey
《紐約日報》獲獎新聞記者,也是超過三十本書的作者,其中包括《The Boys of Winter》,這本書記錄了1980年美國奧林匹克曲棍球隊,同時是《紐約時報》暢銷書。
出版:商周出版(2013年7月)
書名:不死的蝴蝶

目錄:
推薦序一 一種「蝴蝶球」的哲學氛圍∕馮光遠
推薦序二 蝴蝶球到底是怎麼飛的∕朱宥勳
推薦序三 因為存在,所以比賽!∕藍白拖
自 序 最慘的一夜
第一章 出身寒微
第二章 八三年夏季
第三章 皈依
第四章 綠丘孤狼
第五章 志願服務
第六章 封面故事
第七章 孤獨的遊騎兵
第八章 「小」試身手
第九章 大聯盟初登板
第十章 速球輓歌
第十一章 紅鷹再起
第十二章 查理眼中的世界
第十三章 不討喜的蝴蝶
第十四章 谷底
第十五章 勇渡密蘇里河
第十六章 一瞬之音
第十七章 意外的「規則五」
第十八章 求教菲爾
第十九章 棲身大都會
第二十章 彈指法拉盛
第二十一章 愈挫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