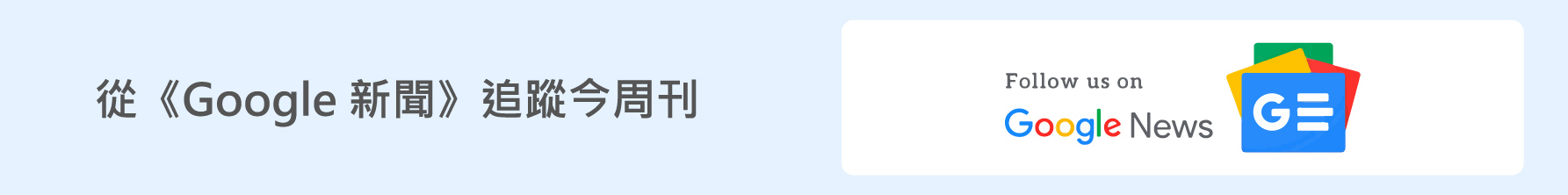失智症是一種進行式疾病。很遺憾地,目前尚未有絕對見效的治療方法,所以失智的年長者們不會做的、不懂的事便會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增加。當然這個過程很痛苦,照護者在認知到這個事實的條件下,必須藉由減法運算,針對各個階段改變與其應對的減法話術。
接下來我將介紹一個略長但易懂的案例,這是在我曾經負責照護的個案之中時間最久的浩一先生。
從發病到最初期
浩一先生以前是一位吉他老師。過去曾在音樂學校接受過正規的訓練,甚至也有出國深造,研習吉他的經驗。直到60歲為止,教過的學生為數眾多。
自從他辭去吉他教室的教師一職後,整個家庭的生計便由上班族的妻子所支撐。在妻子上班時,他會在家中彈吉他、下廚做拿手菜,後來妻子也退休,倆人便會一起去買晚餐的食材,回家後由浩一先生負責料理。他們當時可是過著非常少見的歐美夫婦生活型態。
然而,到了浩一先生75歲時,因為手受傷而吉他再也無法彈出以前的水準。這對他來說似乎是莫大的打擊,從此變得老是關在家裡不願意出門。或許是因為足不出戶的狀態,使得失智症的病情加劇也說不定。
據說他本人也曾認為「自己哪裡怪怪的」。當他到78歲時,由於不希望被其他人認為自己很奇怪,因此更不願意在白天外出。每次都刻意選在清晨或夜晚出門散步,但是返家似乎需花不少時間,推測應該是迷了路。到了80歲時,便遭治療失智症的專門醫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
罹患失智症前的浩一先生是一位沉穩有禮的紳士,然而在診斷結果出爐前,已性格大變,一有看不順眼的事就會勃然大怒。變成一個對妻子總是惡言相向,甚至還會動手打人的「暴君」。不過若是在外頭,行為舉止仍然保持沉穩,也就是說,他只對家人不好。
我和浩一先生第一次見面時,在他身旁的妻子看起來相當小心翼翼,她應該是覺得要是惹他生氣會很麻煩,因此刻意避免去刺激他。
而他本人在一旁倒是裝作一副笑臉迎人的模樣,他頭上那頂為了隱藏髮量稀少的假髮,令人印象深刻。據他的妻子所說,平時他在家裡會把小毛巾綁在頭上掩蓋,只有外出或家裡有訪客時才會戴上假髮。他除了失智症以外並未患有其它疾病,儘管身材短小,但看起來腰腿健壯、身體硬朗。
初期 拜託他來當吉他老師
浩一先生是個對於自己身為吉他手的生涯經歷相當自豪的人。如此高自尊的人,通常不太願意到日間照護機構,然而,考慮到妻子的負擔,家人還是決定讓他前往。
至於該怎麼邀請他,導入的第一步是重點。由於浩一先生還處於失智症的初期,因此如果失敗,讓他認定「我才不要去」的話,等到他忘記這整件事,勢必要耗費更多時間。
浩一先生的人生關鍵字是「吉他」。因此我們針對這一點,使用了減法運算,我們請他前來擔任音樂療法的老師,對他說:
「我們(日間照護機構)這裡有很多因交通事故導致頭部受傷、罹患腦梗塞,歷經手術正在復健的患者。聽說音樂療法頗有效果,想要拜託您前來協助。」
為了讓浩一先生能夠完全相信,為他準備的名牌、鞋櫃等也和一般年長者不同,全部讓他使用工作人員的東西。
當然,就連座位也特別準備了「教師席」,所有的工作人員也都以「老師」稱呼他。因此浩一先生對於自己的身分是老師這點深信不疑(當然我們得配合他努力地演戲)。
浩一先生即使來到日間照護機構,中午以前都是一個人練習吉他。雖然其他年長者也在同一層樓,可是因為他是「老師」,所以大家不能進去他那個房間。中午過後便開始進行音樂療法,即使是這個時段,他也不彈年長者喜歡的演歌等歌曲,主要彈的是古典曲風。
如果對他說:「老師,大家想聽民謠、演歌,或是美空雲雀的歌,能不能麻煩您彈奏?」有時候他願意彈奏,不過途中就會擅自變奏,搞得連我們也不知道是在彈什麼。
若是有人提出:「老師,請演奏大家都知道的歌。」他甚至會露出生氣的表情。像這樣,我們每週讓他以「音樂療法老師」的名義來日間照護機構兩、三次。
中期 假裝發「薪水」
開始往返於日間照護機構後,過了大約快一年,浩一先生表示:「沒有拿到薪水」。
我萬萬沒想到會牽扯到金錢的問題。雖然我和其他工作人員們為了說服浩一先生來,已經使用了各種必要的減法運算,每次也都會提到是請他以「志工」的身分前來,並且還會加上一句「如果什麼都沒給也不太好意思,請讓我們接送和為您準備午餐吧。」讓他順理成章地使用日間照護機構的其它服務。
然而,由於浩一先生罹患的是失智症,因此會忘記自己只是志工。有一次,從日間照護機構回家後,他甚至說:「那裡都不給我薪水!」並把氣出在妻子身上。於是,我們便決定要付薪水給浩一先生,當然這也是「減法運算」的一部分。
首先,我們為浩一先生製作了他專用的印有姓名、領取證明蓋章欄的「薪水袋」。
不過,如果裡面裝的是一疊報紙的話,浩一先生可能會生氣。因此我們便向他的妻子說明原委,每個月由她支付一萬五千日幣,放進信封中,再交給浩一先生。
如此一來便形成了像這樣的流程
1.工作人員先從妻子那裡拿取費用。
2.把那筆款項裝入薪水袋裡交給浩一先生。
3.浩一先生把薪水袋帶回家,交給妻子。
4.妻子拿出薪水,確認後蓋章,並把薪水袋還給浩一先生。
5.浩一先生把薪水袋帶回日間照護機構。
6.工作人員預先向妻子拿一筆費用。
(再度重複整個流程)
後來,由於浩一先生脫口說出:「薪水好少」,我們又再向其妻子說明,把金額提高到兩萬日幣。這個狀態維持了將近一年半,漸漸地他本人很少再提起薪水多還少或有沒有了。
偶爾他還是會冒出一句:「完了,連續三個月都忘了蓋上領取的章,怎麼辦?」但是到了最後,再也沒有提起薪水的話題。失智症會隨著病情的發展,而產生這樣的變化。
從中期邁向後期 即使假髮歪了也不會注意到
浩一先生剛開始到日間照護機構時,完全不願意在這裡洗澡。因為要洗澡的話,就不得不把假髮拿掉,對他而言,這可是個天大的問題。然而,曾幾何時,浩一先生就算假髮歪了也渾然不知。
某一天,浩一先生參加機構的餘興節目時,由於玩得太起勁,身體的動作使得假髮偏到另一邊去。看到這一幕的工作人員擔心浩一先生會不會因此失去控制(這裡指的是失智症患者會失去沉穩、情緒不穩定),然而他本人倒是老神在在。由此可見他的失智症病況已逐漸惡化。
後來終於連在自己家也不太願意洗澡,因此我便放手一搏,建議浩一先生在日間照護機構洗澡。想不到「做比想得還簡單」,對他說了聲:「幫您把帽子拿下來」,然後替他取下假髮,他便很順從地洗了澡。
有時候,他還是會戴假髮,不過當他洗完澡後,即使沒有戴上假髮,他也不會在意。從這裡可以推測出,他大概處於失智症的中期後半左右。
這個階段的浩一先生,似乎已經忘記了「總覺得哪裡怪怪的」不安感覺。在家裡的話,變得不分白天晚上,都會一個人出門散步。
由於他無法靠自己的能力回家,使得他的妻子必須盯著他不可。一旦察覺到他似乎想外出的樣子,就得躲在後頭尾隨他出門,因為要是被他發現自己被跟蹤的話,他會生氣地說:「不要把我當小孩!」
無法獨自上廁所的狀況也越來越明顯,有時候是些微失禁、或者尿在褲子上,有一次,他進去廁所很久都沒有出來,工作人員前去察看時,發現他竟然尿在自己的杯子裡。也就是開始無法正確地使用物品的症狀(醫學上稱為「失認」)。
即便如此,他的食欲還算是不錯,不需要旁人協助就可以自己吃飯,不過拿別人的東西來吃的情形卻屢次發生。這樣的舉動在失智症患者身上相當常見,對當事人來說,位在自己眼前或旁邊等所有在視野裡的東西,通通都是「自己的」。
後期到臨終 日間照護的極限
先前提過浩一先生自從罹患失智症後變得易怒,隨著病情的演變,他的情緒起伏越來越激烈,行為舉止也越來越偏離正軌。在家裡時,人明明在二樓,竟然會說「我要回家了」,然後就打開窗戶想要出去,似乎是妄想的頻率增加。
有一次在日間照護機構時,一位罹患「早老型失智症」的女性,在聽了浩一先生的吉他演奏後,罵他「彈得真爛!」雖然當時還好有工作人員介入緩頰,不過浩一先生似乎對這件事耿耿於懷。事後專車送他回家時,據說他一下車就衝到派出所,向警方報案:「有奇怪的女人毆打我」、「被她踹」等等。
從這個階段起,他衰弱的情形已經相當明顯。他甚至會做出從家裡二樓的窗戶小便、在樓梯上排便等行為,而他的妻子不得不忙著幫他善後。
就連在日間照護機構也會因為一點小事就情緒激動,還會因此搖動桌子、揮舞椅子等。一旦他開始大亂,無論什麼話都聽不進去,就連工作人員要阻止他都很困難。
當浩一先生無法平息怒氣時,我們只好請他的妻子過來,想說是不是看到自己的妻子,就會恢復自我。不過他有時能認得出是自己的妻子,有時卻又認不出來。
由於日間照護機構裡還有其他的年長者,一方面擔心浩一先生大鬧時受傷,另一方面也必須避免讓他傷害到其他年長者,煩惱了很久,我只得告訴他的妻子,浩一先生的狀況已經不是日間照護機構所能應付的,而且就算待在家裡也不會好轉,建議讓他逐漸減少使用日間照護的服務,轉而住進特殊機構會比較好。
他的妻子似乎打算由自己照顧到最後,即使一直幫丈夫的言行舉止善後已讓她疲憊不堪,但仍舊心繫著「只要度過這個困難,就還能再去日間照護機構」的想法,因此努力地在自家照護他的生活起居。
然而在與主治醫師討論後,她終於心不甘情不願地選擇「放手」。之後,浩一先生歷經了住療養病房,最終被送進專門醫院。
一開始,這位妻子花了很多精力和時間去和他會面,打算彌補不是由自己照護的缺憾,頻繁地往返於醫院。
儘管浩一先生變得稍微消瘦,不過看起來恢復到以前沉穩的樣子,據說妻子對正在睡覺的他說話時,他聽到聲音醒來就會很開心地回應:「來了啊!」但漸漸地,他卻表現出一副「知道是認識的人但不知道是誰」的態度,也越來越無法言語。
無論是哪一種失智症,最後都會臥病不起。先前的狂風暴雨過去後,浩一先生也在醫院裡安穩地度過最後一刻。
妻子自從陪伴他這麼長時間以來,留下了一些習慣,其中一個是「真拿他沒辦法」的口頭禪,指的是對於「說什麼道理都不會懂的人」無論說什麼也沒用。聽說她花了相當久的時間,才調整成這樣的心境。
另一個習慣是「大聲笑」。對於容易做出各種粗暴舉動的浩一先生(這也是失智症的症狀之一),只要聽到妻子的笑聲,情緒就能夠平穩下來。
但若光只是臉上有笑容,可能會因為兩人所在的場所不同,而無法傳達給浩一先生,因此她會刻意發出聲音大笑。
送走浩一先生後,妻子最終說出:「我已經照顧夠了,所以一點也不後悔。」對於照護者來說,這一句「不後悔」是相當貴重的話語,就連陪伴在一旁的我來說,也是比什麼都還要值得高興的評價。
(本文摘自《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第一本專為照護失智症所寫的減法話術!(安心長照必備‧全新封面版)》,蘋果屋出版,右馬埜節子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