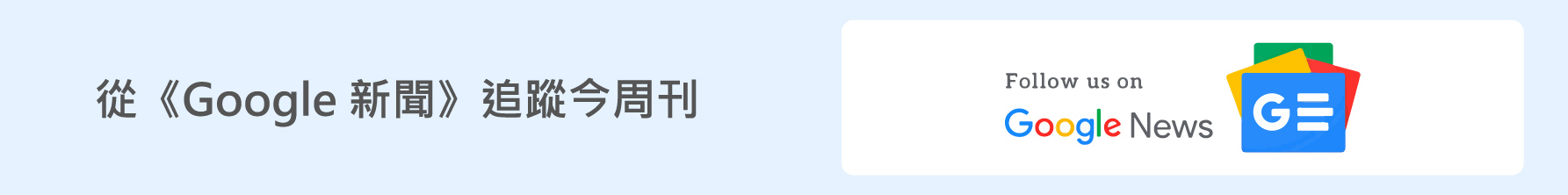溝通無非編碼與解碼,如果缺乏「可交換或共同認可的」符碼,交流根本無法推展;而葡萄酒溝通或者社交最基本的符碼,就是葡萄酒的名字。
某天,一位朋友帶來法國波爾多產區的Château Choteau,我一看酒標就笑了,以法語念出酒莊名稱,然後打趣地說:「這,不是『秀逗』酒莊嗎?」
旁邊聽到對話的人也都笑開了,帶酒來的朋友大聲抗辯:「中國那邊的譯名才不像你這麼沒水準,人家翻譯成『秀都』酒莊!」
美酒妙趣,非關文字?
朋友的反駁提醒一個有趣的現象:台灣進口的葡萄酒並不強制將名稱譯成中文,彷彿每一位愛酒人都「應該」能夠自由閱讀英文、法文、義大利文……似的。在某些圈子裡,甚至因為法國葡萄酒的獨特地位,法文酒莊的讀音是否標準,有沒有濃厚的英文腔,竟成一種是不是「內行人」的另類判準。有人就跟我抱怨,曾上過一期品酒課程,「簡直就像在上法語正音班!」
葡萄酒的名字真這麼重要嗎?莎士比亞不是說過:「玫瑰即使叫作別的名字,依然甜美。」(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為什麼不能就直觀地享受葡萄酒的美好,非得這麼在乎名字呢?
禪宗一個著名公案的看法也很近似:唐朝六祖慧能行腳至韶州,受到一位名叫劉志略的儒士禮遇,儒士的姑姑出家為尼,常誦《大涅槃經》。六祖經過聽說經文,深解妙義,就為她詳細解說。比丘尼非常高興,於是手捧經卷逐字請益,六祖卻表示自己並不識字,無法讀經,但願對話解釋義理。
這位比丘尼驚嘆道:「字尚不識,焉能會義?」
六祖回答饒富深意:「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的確,最超脫的覺悟就像是最美好的體會,是個人生命的深刻經驗,表象文字反而是一種拘泥限制。
但對於在「先於個人存在」社會生活的我們,葡萄酒名字蘊含的重要意義,至少我以為有四個原因:
葡萄酒的社交與解碼
首先是為了辨識。想從浩瀚無垠的全球葡萄酒市場準確地找到「那一款酒」,在這個資訊爆炸、比從前複雜不知道多少倍的時代裡,不認識心儀標的的名字,「巧遇」機會幾乎為零。
再者,從名字上可以解讀這款葡萄酒的出身源頭,了解它的歷史背景;有時還可以釐清賜名的酒莊主人對於這款酒的期待,很快的——雖然的確有造成誤解的風險——就能為它在葡萄酒市場上找到大致的定位。
第三,葡萄酒當然可以獨享,但它在歐洲文化傳統上有很濃厚的「社會性」與「社交性」,因此分享與溝通,成為品酒完整經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但溝通無非編碼與解碼,如果缺乏「可交換或共同認可的」符碼,交流根本無法推展;而葡萄酒溝通或者社交最基本的符碼,就是葡萄酒的名字。
最後,談溝通符碼,我們不可避免地要面對法文。
法文,這種曾經是歐洲上流社會或外交場域的流行語言,雖已不再強勢,卻彷彿因此閃耀著沒落貴族的神祕色彩。現代人眼中詰屈聱牙法文書寫的酒標,活脫脫就是一種到今天依然執掌葡萄酒正統的舊歐洲之文化古老密碼。這種密碼有一種奇特的魔力,能反映出法文以外世界文化團體裡,對於不可解的驕傲密碼之疏離、不安與焦慮。
不過矛盾的是,若能明確具體化這些焦慮,反而能削弱古老文化所造成的神祕壓力。因為焦慮成為一種具象,有名字,面貌清晰可辨,我們就能控制它,甚至為我所用。
社會學稱這種認識名字的文化過程,叫「倫佩爾史提爾斯金原理」。
倫佩爾史提爾斯金(Rumpelstilskin)是格林童話裡的邪惡小妖精,擁有不可抵抗的魔力,喜歡傷害小孩子。但是要是知道它的名字,並且大聲喊出來,這惡魔就會立刻喪失力量,並且逃之夭夭。
真是很有意思的童話,不是嗎?
在渺小個人常常承受著莫名集體壓力的時代,「倫佩爾史提爾斯金原理」似乎比莎士比亞或六祖慧能更有啟發性?所以,我的朋友,不是「秀逗」,亦非「秀都」,大聲念出Château Choteau!
(本專欄由楊子葆、焦元溥、焦桐、艾予森共同主持)
楊子葆
一九六三年出生於花蓮,法國國立橋樑與道路學院(ENPC)工程博士。曾任新竹市副市長、台灣駐法國代表、外交部政務次長等職。精葡萄酒、交通學,也是一位法國通。